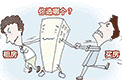各位同學,大家上午好。
很高興有機會與在座的研究生分享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今天我採用的標題是我5年之前在和2010年入學的研究生分享體驗時用的標題——“少年壯志不言愁”。這是一首電視劇的主題曲,也是我最喜歡唱的一首歌曲。
我想講的第一部分是我的成長之路。
以前我在講這一部分的時候會講得特別長,而今天這部分隻有一張幻燈片。
在座的有些同學可能還沒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麼,會感到焦慮:如果對科研不感興趣、沒想好未來發展該怎麼辦?其實我想講的是當我在你們這個年齡的時候,也就是二十幾年前,我也沒有想好,也非常迷茫。這種迷茫一直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才隱約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才下定了決心。
當時的迷茫來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學選擇專業。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學入學時就知道自己想學什麼專業,想學經管、建筑、生命、化學、工程,等等。我當時保送大學,報名的清華的第一專業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機械系(掌聲)。
在報機械系之前還報名了北大的物理系。直到85年5月份清華老師來招生時對我說,生物化學是21世紀的科學(掌聲)。我當時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學連接在一起,當時突然覺得豁然開朗——原來生物化學是21世紀的科學!於是陰差陽錯地上了生命科學這條船。
我是數學競賽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華,數理能力很強。在座數理能力比較好的同學可能有同樣的糾結,數理好往往學生物、化學不靈。我曾和生物學競賽的同學講,千萬不要自卑,數學物理競賽好的是有小聰明,生物競賽好的有大智慧。
這種說法是有爭議的,我今天說的很多內容可能都有爭議。學習數學物理著重思維的嚴謹,注重推理,而生物不同,這些發生在不同的腦區。我在清華的時候生物學的不好,於是修了數學雙學位,通過加強數學物理課程的學習來彌補生物成績的不足,來讓我的成績排名第一。所以說,我選專業第一不是憑興趣、第二不是憑專長,而是憑清華老師的一句話(笑聲)。當然這是一句玩笑了。
那選專業應該憑啥?我告訴學生,憑未來世界的需求。這個世界的發展不以在座的某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媒體宣傳為轉移,更不以畢業之后能否找到工作為轉移。這個世界的發展中,一半以上的學術問題來自對人類的關注,叫做生命科學。
不管國內就業情況怎麼樣,其他學科情況怎麼樣,但大生命學科在21世紀是最大的學科。你們可以去查查,麻省、斯坦福、哈佛最大的學科是什麼。我覺得在你選擇專業的時候,憑興趣挺好,沒有興趣的時候可以培養興趣。有時我在想,人是善變的,你的其他方面可以變,為什麼專業是不能變的?
一項業余愛好可能你很喜歡,但天天做可能會使你厭煩。我認為做一件事,完全憑興趣的話,對我而言不靠譜。大學期間我對生物真的是深惡痛絕,因為學不好。我的遺傳學實驗、遺傳課、細胞學實驗、細胞課在班上都是中下。
本科講完,我來講一講海外讀博。我在清華提前一年畢業,那是在89年。當時我對學術沒有興趣,而對從政感興趣。可能有些同學了解,當時我父親的去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認為從政可以改變一個社會,可以為老百姓說話、做事。
我當時想去從政。而從政又沒有門兒,覺得要先去經商。所以當時和清華大學科技批發總公司簽訂了一個代表公司去香港經商的機會,做公關(笑聲)。你們難以想象吧?看這施老師還挺能說會道的,做公關應該還不錯。我年輕的時候比現在強太多了,結果就業合同因故被撕毀。
89年7月24糾結一晚后,我決定考托福GRE出國。在年輕的趾高氣揚的施一公心裡,出國不是一條路。最終我決定出國讀生物學博士。在霍普金斯的5年讀博期間很辛苦,尤其前兩年心情很不穩定。由於我數理思維太嚴謹,常常繞不過這個圈,總覺得學生物怎麼這麼難。
有一門生物學考試三次考試52、32、22分,隻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師放我一馬:“我是一個好學生,對學生物還在適應。如果我不及格的話,我會失去獎學金,沒有獎學金的話我會讀不下去,隻能退學。”他戴著眼鏡瞇著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個好學生(笑聲)。他最后給了我一個B-,我對他真的非常感激。
在普林斯頓做助理教授時,我第一次回霍普金斯講課的時候,我去拜訪這位教授。我問他,您還記得我當時求您放我一馬給我及格嗎?他說,我怎麼能忘記呢!(笑聲)其實因為我對專業沒有想好,在讀博的前兩年一直非常糾結。平時精力很好,一看文章就睡著﹔聽講座也是,聽了十分鐘就睡過去了,大家一鼓掌我就醒了,正好大家一塊走。(笑聲)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會這樣。
我直到博士三年級才出了一點感覺,發現我也能做一點東西﹔到了博士四年級信心大增,因為結果出來了﹔到了畢業那年,博士五年級,我感到,原來我也可以在學術界“混”個工作。
博士讀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會干啥,在最掙扎的時候曾想過轉系:轉數學系、轉計算機系、轉經管系,轉任何一個系我都覺得易如反掌,因為這些都是能發揮數理長處的地方,但我沒有轉。因為我在說服自己,也許以不變應萬變最好。如果急急忙忙轉系,也許去了之后會發現數學、物理、經管可能更沒意思,所以我在說服自己,也許生命科學真的是21世紀的科學呢。
就是一種在矛盾中在往前走。在1995年4月12日博士學位答辯以后,我還是不清楚自己會做什麼。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在清華的時候,曾是清華活躍的一分子,小發明協會的副會長,還參與了很多課外活動,做公關,所以我想也許我可以從商。所以我還面試了大都會中國區首席代表的職位,賣保險,而且拿到了offer。我差點成為中國第一個賣保險的人,當時有六位數的工資。
在博士畢業之后我還設立了自己的公司,和兩個哥們一起做中美間貿易交流,這個經歷也很有意思。1995年11月我下定決心還是走學術這條路,到現在還不到20年。95年12月我寫了一篇日記,我說,該去explore的機會,你也都explore了,現在輪到你靜下心來,從此之后不再起二心,好好做學術。我也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從95年11月到現在,所有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學術上,我也告訴自己這(種興趣)一定可以培養起來。在座如果有同學感覺對所學領域沒有興趣的話,我想你比不過我。我是在博士畢業半年之后才開始培養興趣,現在我的興趣極其濃厚,到現在可以廢寢忘食、可以沒日沒夜地干,覺得樂在其中。我覺得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不是說你天生就有,不是說你聽一個講座突然靈機一動就對一件事感興趣,我覺得都不是這樣。
博士后這幾年在外人看來極其苦,其實自己身在其中並不覺得苦,我經常覺得自己不這麼做的話就虧了。我確實是這樣想的。95年11月到97年4月,我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頓做助理教授的機會。當時挺幸運的。
普林斯頓不像哈佛大學那樣有很多學院,像醫學院、法學院等等,而是隻有一個大學本部加一個國際關系學院,很小。我認為普林斯頓是一個學術聖地。這也是為什麼愛因斯坦在面臨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美國多所大學邀請的時候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普林斯頓,可能去過的人會有感受。我覺得我挺幸運的,97年4月在普林斯頓開始獨立的科研生涯。
其實我對專業、對研究曾經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彎路,但我覺得我還是走過來了。我也勸在座的同學,當你有迷茫的時候,我建議你們,不要覺得隻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問題解決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認可。
我認可一點:不要給自己理由——當你覺得興趣不足、沒有堅定信心、家裡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陰影、面對痛苦往前走的時候,不論家庭、個人生活、興趣愛好等方面出現什麼狀況,你應該全力以赴,應該處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給自己理由。因為你一旦掉隊了以后,你的心態會改變,很難把心態糾正過來。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