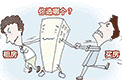火車穿過漆黑深長的隧道,馳過廣闊的插著稻草人的田野,繞過蔥郁巍峨的山,一路向延安奔去。至此,重走西南聯大之路暫告一段落。回首過去大半的旅程,長沙和昆明的一幕幕依然鮮活清晰,彌漫著歷史的厚重和深沉。岳麓書院門口,“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的對聯飽浸千年滄桑而豪氣不減﹔雲南師大校門上,“剛毅堅卓”四字校訓依然蒼勁有力,閃耀如火光﹔西南聯大舊址內,當年的鐵皮房火腿椅猶在,只是不見了當年目光炯炯奮發圖強的青年。一路走,一路聽,一路記,山河破碎、烽火連天的大背景下,每個渺小的個體為家國拼盡全力的故事讓我唏噓不已,也慶幸自己有機會了解到如此珍貴的歷史片段。
然而,比起恢弘而悲愴的歷史,更讓我感動的是每次參觀和座談時與我們分享的人。他們就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或許是身處特殊的環境給了他們特殊的使命感,對那段歷史,他們非但不能釋懷,反而抱著一腔赤誠,奔走呼號,希望更多的人銘記和深省。他們,只是無數群眾中再平凡不過的一員,是浩瀚歷史海洋中渺小的一滴水,卻以自己的方式散發出了珍珠的光芒。
親歷者:一切以國家需要為准則
孫亮老先生是雲南師范大學物理系離休教授,現已92歲高齡。去採訪他之前記者團在參觀西南聯大紀念館,我沒留意時間,遲了幾分鐘才趕到。一進門爺爺正在屋子裡踱步,步履矯健,見了我們便坐下來詢問我要採訪些什麼,思路清楚聲音洪亮,完全沒有耄耋之年老態龍鐘的姿態。我表達了想了解他在西南聯大的求學歷程的意願后,老先生微微頷首,說前幾天有人採訪他的時候他也講述了自己從小到大的求學經歷,不如也從頭給我講一遍。
孫老先生與西南聯大的淵源頗深,求學之路卻曲折輾轉。他從小成績優異,卻因家境貧寒不能到條件更好的公立中學讀書。1942年,西南聯大在昆明建立了附中,並開始招收通過考試的插班生。按捺不住心中的羨慕和向往,孫老先生在次年報考,並成功成為了高二班級的一員。隨后他順利進入西南聯大學習,因為當時國家需要電訊方面的人才而選擇了電訊專修科。然而好景不長,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孫亮迫於家庭經濟壓力沒能和同學們一起回到清華大學繼續學業,隻好留在當時的昆明師范學院。在校期間,他再次為了國家危機的形勢投身學生運動,並成為地下黨,被派到滇北地區工作,甚至不惜中斷學業。直至建國后多年,老人才等來了那份沉甸甸的畢業証書。任職雲師大教授以后,孫老先生依舊兢兢業業,培養出了多名院士和專家。
作為當年崢嶸歲月的親歷者,面對一批又一批前來求証探尋的人,老人必然已經將自己的人生講了不知多少遍。或許他所感知的只是那個大時代的冰山一角,卻依然為當年的傳奇平添了一份真實。更重要的是,老先生一生中所有的重大選擇都以國家需要為准則,這份情懷和熱血就足夠崇高,足夠讓后世景仰。
守護者:如果沒有我,不知誰還記得
在昆明的大部分行程都由吳寶璋教授陪伴。這也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他是雲南師大歷史系教授,對西南聯大的歷史鑽研多年。初見吳教授是在雲師大的講座上,他為大家介紹了西南聯大的歷史。當時我並沒有覺得這位老人有什麼特別,也正因如此,在第二天真真切切地被他感動。第二天是計劃好的徒步十公裡,沿途參觀當年的多個遺跡和西南聯大時期的名人故居。吳教授一路隨行,帶領記者團穿梭在隱秘的居民區、老市場中,找尋那些被層層遮掩的、或已翻修或已破敗的房屋,每到一處都親自給大家講解故居的歷史和現狀。在潘光旦故居前,望著頹圮的牆、破碎的磚瓦和滿院泥濘垃圾,吳教授聲音悲愴:“就連我來也要找好半天,不知道還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了。”他寄希望於我們,希望大家能幫忙促成這裡變為文物保護單位,得到應有的修繕和保存。
同樣的還有湖南大學的姚諍老先生。82歲高齡的他曾是校園裡的綠化美化干部,不僅熟悉校園裡的一草一木,更終生致力於讓所有人了解日軍侵華的歷史。聽說記者團來訪,他自告奮勇來給學生們講解。老人穿的很朴素,白發整齊,掏出的手稿工工整整。他給學生們講解和平樓民主樓被炸的歷史,也講自己設計建造的紀念廣場。1997年,校園裡曾挖出三枚當年沒有爆炸的炮彈,公安部門出於安全考慮打算全部收繳,姚老先生卻執意要留下來一顆展示出來作為對歷史的銘記。他還親自跋涉到外地,挑選了雄獅形狀的石頭置於廣場正中,寓意“東方醒獅仰天長吼,震懾西方帝國主義”。談到自己的杰作,老人有些自豪也有些羞澀:“原本應該已經建好的,但因為安全隱患可能要推遲一陣子了”。他最終還是為了大家的安全妥協,同意做一個等比例的炮彈模型展示出來。
兩位高齡老人,在不同的城市做著同樣的事。他們痛心於歷史的消逝,恥辱的淡去,隻能以一己之力守護殘存的曾經,把故事講給更多的人,也在不經意間感動了很多人。
傳承者:做不到創新,至少要保留
在雲南大學座談的時候,主講人是黨委副書記張昌山。我以為他的講話和對問題的回答是最誠懇最實際的。走訪了一路,耳邊最不缺的便是歷史,而張昌山副書記卻站在自己的角度深刻地反省了現實。講過了雲南大學在抗戰時期與西南聯大相互扶持相互學習的輝煌歷史后,他自己首先提到了那個有點難堪的話題——為什麼曾經輝煌的雲南大學如今籍籍無名難以振興?他不否認學校后來發展中出現的弊端,不否認浮躁的社會氛圍使老師不能用心教、學生不能用心學,語氣裡有無奈也有遺憾。然而他也自豪地告訴我們,雲大要“頂天立地”,既要服務雲南本地,也要打造世界級學術。在各所高校爭辦世界一流大學、隻看前方不顧腳下的今天,這種腳踏實地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張昌山直言,雲南大學的創新能力是不夠的,但即便做不到創新,他至少要保留、要傳承,西南聯大的精神不能丟。
更年輕的傳承者們還包括各個博物館、紀念館的講解員,他們當中很多只是普通的大學生,抱著鍛煉自身的目的參加了學校校史講解的社團,卻迅速披上了一份責任感。
感動於歷史,更感動於這些普通人。每一滴水都是歷史海洋裡的珍珠,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光芒,這光芒也將照亮我,再由我傳遞下去。(北京大學 金畔竹)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