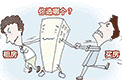6月6日,盲人考生王香君(左)在母親的陪伴下來到合肥世界外國語學校考點查看考場信息。今年18歲的王香君是安徽省藝術職業學院音樂系中專部的學生,從小熱愛鋼琴的王香君希望通過高考能在音樂的道路上繼續深造。 新華社記者 劉軍喜 攝
編者按
從恢復高考后到2013年,有6000多萬大學畢業生走出校門,他們每個人的汗水和智慧匯聚在一起,改寫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命運,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一個時代的走向。
所有的這些改變,最初起始於1977年的那一場考試。也許,高考前的通宵復習,曾折磨得你難以承受,也許,最終的放榜結果,不可能人人滿意,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種相對權威和公平的人才選拔方式。
30多年來,不斷完善的高考制度,以及其背后的一整套考試招生體系,對提高教育質量、提升國民素質、促進社會縱向流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當下,社會成員終身學習通道正在被逐漸拓寬,高考“一考定終身”的格局也已經被打破。隨著高考改革的逐步推進,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將更加有助於培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多樣化高素質人才。
今天,2015年全國高考開考,942萬考生步入考場。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每十萬人口中,隻有615人接受過大專以上教育,那一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學生,剛剛走上工作崗位。在后來的30多年裡,他們中的許多人,成長為國家建設的骨干力量,現在,他們陸續到了退休的年紀。
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時,我國每十萬人口中,有8930人接受過大專以上教育,是1982年的14.5倍,並且,這一數字還在逐年增加。那一年的畢業生,如今已經步入而立之年。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2013年,我國各級高等院校本專科招生總數超過8000萬人,高考,改變了這8000多萬人每一個人的命運。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高考故事,而每一個高考故事的背后,映射著時代變遷。
高考意味著“回城”
時間:1977年至1979年
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數:27.3萬,40.2萬,27.5萬
參考者:吳濱,福建人,現為福建省某機關干部
關鍵詞:恢復高考
再過幾個月,吳濱就要退休了。“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現在的吳濱,是機關裡的處級干部,而他高考前工作的單位,早已倒閉。
1969年,吳濱隨著父母下放到了福建閩西山區,高中畢業后,他隻能去當知青。1976年,他到了當地一家部隊建制的機械企業當工人,企業裡有3000多名職工。“住草棚,屋頂上鋪著毛氈,企業離市區幾十公裡,生活、娛樂設施都極差。”
吳濱以為,自己可能一輩子就在這裡了,他憑著文筆,成了廠裡的通訊員。雖然做夢都想上大學,但也隻能拿起書自己看看。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在工廠裡“炸開了鍋”,“從得到消息到高考不到半年時間,當時連課本都借不到!”吳濱說。他的父母已經調回福州,到處托人找復習資料,最終通過上海的親戚才買到了一套。“在當時千金難求呀!”
“白天要上班,晚上點著煤油燈,沒看幾頁書,上下眼皮就打架。准備考試的人很多,有的上半夜復習,有的下半夜,剛好資料可以一起用。”吳濱說。山區蚊子多,他們把腳泡在水桶裡,不僅防蚊子,還能清醒提神。“工資隻有18元,扣完伙食費,其余全部用於文具和營養品。”
第一年,一心想當科學家的吳濱報的是理科,分數上線了,還參加了體檢,但最終落榜。第二年,吳濱更加勤奮,“連最喜歡看的電影都不看,除去上班,所有的時間我都不輕易放過。”結果連分數線都沒有達到,
1979年,高考形勢大變,過去以“老三屆”為主的考生隊伍,變成以應屆生為主,招生人數也減少了13萬。“我們跟應屆生比,基礎差太多。”吳濱改考文科,如願考上,並成了全廠的文科狀元。
“我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吳濱說,當年他所在的企業早已倒閉,沒有高考,現在的命運可想而知。“高考還是一種‘精神’,讓我明白,人生要有目標,同時還要有毅力,堅持下去一定會得到回報的。”
高考意味著“吃商品糧”
時間:1982年、1983年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數:31.5萬,39.1萬
高考人:李建功,河南人,職業教育學校校長
關鍵詞:城鎮戶籍,干部身份
李建功至今記得,自己被錄取后父親的狂喜,一向少言寡語的父親把他抱在空中,蕩了一圈,激動地說:“我家出了狀元了!孩兒啊,你以后就是吃商品糧的人了。”小腳的祖母則跌坐在了門口,激動地淚流滿面,喃喃道:“俺孫子出息了……”“從來沒有見過祖母這樣幸福地流淚。”李建功說。
李建功是農業戶口,在上世紀80年代初,農業戶口和城鎮戶口有很大區別,城鎮戶口能吃商品糧,享受一定待遇,工作往往也是“鐵飯碗”。對於農村子弟來說,高考,是拿到城鎮戶口的僅有機會。河南是農業大省,人口眾多,高考就成了“千軍萬馬過獨橋,為了一口商品糧”。
剛開始的時候,李建功並沒有考的勇氣,因為高中畢業已經好幾年。當時,他在縣裡的糧店做搬運工,看到幾個同事考上了,於是決定參加。
1982年李建功第一次參加高考,書揣在褲兜裡,白天搬糧袋的間歇、吃飯的間歇、還有晚上的時間,都用來“見縫插針”復習,但還是沒有通過預選,第二年,“卷土重來”的他通過了預選,拿到了高考資格。
從預選到正式考試有一個月的時間,李建功干脆辭職復習。“那段時間,我早晨四點半起床,到學校操場上跑幾圈,然后拿上書,坐下來背誦。”早晨,空氣清新,一邊讀書,一邊看著樹葉晃動在地上留下的斑駁,李建功現在想起來,依然覺得那是件極愜意之事。最終,他被省城的師范學院錄取。
畢業后,李建功被分配到市政府工作,在第一批公務員下海潮中,他當過房地產開發商,后來又成了職業學校校長。有時候李建功總在想,從師范學校畢業到最后回學校教學,就像輪回一樣。“三十多年過去了,那一年的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也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今年,我的學生也要參加高考。不知道多年之后,當他們再回憶今天,會是怎樣的記憶?”
如今,“商品糧”一詞已經走入歷史,隨著職業教育體系的不斷健全,高職單招試點正在有序推進,越來越多的考生,已經把職業院校,作為自己的報考志願。
高考意味著“不再窮下去”
時間:2000年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數:220.61萬
高考人:張俊,湖南人,創業者
關鍵詞:擴招
“那一剎那,你覺得人生有點戲劇性的。”
2004年,本科畢業的張俊,到廣東富士康所屬工廠做一線管理。上班第一天,他就在生產線上發現了高中同學王某。兩人畢業於湖南一所有著“高考工廠”之稱的高中。“她是班裡唯一沒有考上的,我則是倒數第二名。”
張俊一直是“淘孩子”,學習成績欠佳,初中畢業隻能上職高。“我爸沒出聲,抽了一堆煙,”張俊家在山區,耕地少,父親身體又不好,家境貧寒。后來,他的父親去求遠房親戚幫忙,借了一萬元擇校費,把他送進了高中。
“按照我的成績,考大學是沒希望的,但我爸也想不出來有什麼辦法能讓我不再窮下去了,讀書在當時是唯一的路。”當然,這一萬元,對於貧寒山區農家來說是天價債務。
高中三年,張俊的成績一直是“后進軍團”、“剛開始還覺得對不起爸爸,努力學,但大家都努力,也沒什麼效果。”但是,“擴招”眷顧了張俊。
1999年,我國高校開始第一次擴招。1998年,高招錄取人數為108萬人,2000年則增至220萬人。
“我的大學是撿來的。”張俊的錄取通知書讓父親激動地流下了眼淚。“他可能覺得我能躍出苦的‘農門’了。”
2004年,大學畢業生已不再分配工作,畢業於理工院校的張俊同樣南下打工。去廣東,是湖南、四川青年的主要選擇。隻不過,大學生到工廠是當干部,高中生隻能做操作工。與倒數第一名在流水線上戲劇般相聚,兩人激動而又尷尬,但身份已經是天壤之別。
曾經的“淘氣孩子”,工作后一樣閑不住,在富士康工作幾年后,張俊很快利用電氣專業知識,創立了一家電氣工程公司,兩三年后資產達到千萬元。后來,他被一次拖欠嚴重的三角債拖垮,血本無歸,很快又二次創業,創立了一家服裝外貿企業,如今經營得風生水起,產品遠銷歐美,並且持有自有品牌。
“淘氣孩子就是能折騰,最多就是失敗,不怕失敗。”張俊坦言,“高考把我帶到了這個充滿機會的世界,它隻改變了當時的境遇,但並不意味著永久改變。如果我沒考上大學,我還會創業,現在農村創業成功的比比皆是。”
高考意味著“到北京”
時間:2001年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數:268.28萬
高考人:孫光,黑龍江人,中信高級經理
關鍵詞:素質教育,3+X
1999年,《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發出,那時孫光還是哈爾濱第三中學高二學生。這所中學因推行素質教育而知名,歌手李健畢業於此。李健和孫光一樣,都曾是中學藝術節的“焦點人物”。
1998年,高一時的孫光在音樂鑒賞課上迷上了帕瓦羅蒂,從此拜師學男高音。“高二時,聽說有文藝特長加分,抱著試一下的想法,我到清華北大踩點兒。”2000年春節前,孫光第一次到北京。1月的哈爾濱,孫光要穿兩條棉褲,而北京隻用一條秋褲。“那一刻,我就想一定要到北京上大學。”
為了得到錄取機會,2001年1月,孫光分別參加了北大、清華、人大、原北方交大的藝術冬令營。后來原北方交大給了他降分政策。
那一年恰好是“3+X”改革的推廣年,推廣省份包括黑龍江。“高考每一步改革,對於第一年趕上的考生來說,彷徨感最大。” 每天早上6點起,夜裡12點睡,備考的日子,支持孫光堅持下來的,就是北京冬天裡的那份溫暖。
最終,孫光以錄取成績第二名考上了。“沒用上特長加分,但藝術素質教育也讓我的人生不一樣了。高考至少是一次較為公平的較量。有了高考,我才有機會來北京。”
孫光在大學裡參加了央視的比賽,室友們也因他的特長而喜歡上了歌劇。盡管從事金融工作,但他總覺得藝術教育受益匪淺。
從今年開始,高考的體育、藝術等特長生加分被取消。
高考意味著更多選擇
時間:2014年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數:698萬
高考人:周思含,北京師范大學學生
關鍵詞:自主招生
關於去年剛經歷的那兩天高考,周思含的記憶是這樣的:數學考完有些人哭著走出來、全部科目還沒考完就有人撕書……
周思含保持了輕鬆的心態,因為她參加了自主招生考試。“我們文科實驗班18個人,有十個人都參加了自主招生考試。”參加自主招生考試就多了一道保險,按照協議要求,許多人隻要過了重點線就可以上心儀的大學。
周思含在高考中超常發揮,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她的兩個同學雖然發揮失誤,但仍依靠著自主招生協議,進入了預期學校。
這樣皆大歡喜的結局在幾年前很難出現,周思含的高中班主任告訴她,過去全校分到的名額隻有四五個,隻能照顧到最優秀的學生,而非真正有特長的學生。
現在的周思含,正在讀大一,每天的生活被課業、學生活動、志願服務擠滿。被問及是否適應大學生活時,她的笑容一下被點亮,“太適應了,我都一點兒不想家。”她說。
本報記者 吳鐸思 趙劍影 羅娟 於宛尼 本報實習生 黃潔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