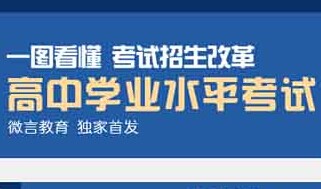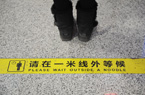透過北京朝陽區萬通中心AB座2層一間診室的落地大玻璃,可見林立的高樓扑面而來。40多年前,鄭偉從這座城市離開,那時的北京還是另一副模樣。“好多年沒有講普通話,想回來說說鄉音,畢竟這是我從小長大的故鄉。”在香港、澳大利亞、加拿大求學、工作之后,在知天命的年紀,鄭偉選擇回到故鄉。
回國工作是“一次挑戰”
2013年7月,鄭偉以新任外科主任的身份,來到北京和睦家醫院。在此之前,他是被稱為澳大利亞八大院校之一的墨爾本莫納什大學的兒外科講座教授,也是莫納什兒童醫院兒外科主任。
在澳大利亞既能做研究,又能兼顧臨床診斷,為何轉而回國發展?對鄭偉的這一選擇,有人不理解。“我回國不是隨大流,隨大流就不會有今天。”在他看來,回國工作是“一次挑戰”,但還是想嘗試一下。
對這個“挑戰”,鄭偉做過仔細考量。“我在國外講英文或中文,都沒優勢。如果在國內,雙語會有優勢,而且國內的發展非常快,可發揮的空間大。你能想象5年后的北京是什麼樣嗎?”
“但回來后是不是什麼都會像我想象中那麼順利?”鄭偉反問自己。他的答案是:不順利也不打緊,與其從來沒試過,不如試一下。“反過來,一個崗位一直做下去,機會就會受限了。我們讀那麼多書,怎麼反倒把自己局限起來了?”
無論得失,鄭偉已經在新崗位上開始工作,並把國外的醫學理念融入到實踐中。比如手術前,大家要先討論﹔每周舉行兩次學術講座,並且要總結梳理醫生們接觸到的各種病症等。
赴安哥拉做志願醫生
相比回國工作,鄭偉另一個“不隨大流”的選擇是2000年赴非洲安哥拉做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志願醫生。那時他正在香港大學工作。對他的選擇,很多人同樣不理解,包括他的父母。“甚至有人說我是傻子。”
鄭偉的擔心是再回不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但志願醫生一直是我想做的,通常志願醫生中年輕人或者已經退休的居多,處於二者之間的少。我想自己既有經驗,年齡也不是太大,這個時候去,對病人、對自己都是最好的。”
當時的安哥拉正在打內戰,14個人的志願者醫生團隊中,大多醫生來自歐洲,隻有鄭偉一個華人。“我們是為了當地的難民而去,一般會處理三類病症,一類是因為當地有地雷,平民踩中地雷負傷或者戰傷,這樣的情況佔到約1/3﹔第二類是因貧困和衛生條件差引起的各種感染病﹔第三類是基本的外科病。”
1年的志願醫生經歷讓鄭偉“終生受益”。“看到當地難民的生存狀況,比比自己,覺得什麼難事都不算什麼了。”
回到香港,鄭偉確實沒有再回到自己原先的工作崗位,但他父母的態度卻已完全轉變。“我去非洲時,父親非常反對,感覺壓力很大。但我回來后,他卻以我去過非洲為傲。”
43歲開始攻讀博士學位
正是在非洲的經歷,讓鄭偉在43歲“有膽量”放下工作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是我下決心最大的一次選擇,甚至不知道讀完之后能不能再繼續從事之前的職業,但最終覺得隻要自己喜歡就值得去做。”
當時他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因為犧牲了好多去做這件事,必須要做好,但好在自己有臨床經驗這個優勢。”
回憶起5年的博士生生活,鄭偉覺得那是自己思想最自由的階段。“有些基礎研究類的文章第一次讀,要四五遍才能讀懂。因此一篇10到20頁的文章,我會花一天時間反復去讀。當時我對自己研究領域的所有文章都熟悉。一輩子清醒地活那麼一段時間很值得。”
在博士階段,鄭偉的研究方向是p63基因和膀胱外翻的關系,根據該研究完成的論文發表在了影響力很高的雜志上。2012年,由鄭偉帶領的博士及博士后團隊發現了p63基因在膀胱外翻這一先天性畸形中的作用。
在發表文章問題上,鄭偉的原則是“不求多,隻求精”。“一生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這種想法也是他現在帶國內學生的理念,“我不希望改變他們,隻希望自己這種務實的態度能對他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郝 青攝)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4年01月10日 第 11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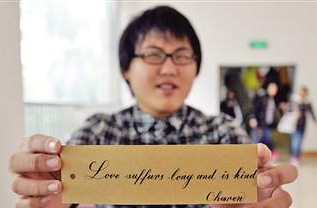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