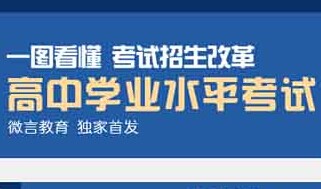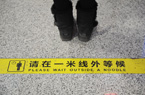来往的火车呼啸而过,载回一批批游子,有些梦就安在这些心上,随着一路的颠簸,伴着一路的风景,染上家乡的颜色。然而那些面色焦急贪婪地搜索着似曾相识的景物的多半是中年人,少年的心还在远方飘着,稚嫩光滑,不那么需要家乡的抚慰和修复。
我们这些离家不久的大学生若是想回家,那多半是想念家乡的食物,想念父母的疼爱,想念没有考试放松玩耍的环境。到家后便行李一丢,床上一躺,再打个滚,就不愿意起来了。晚上不睡早上不醒,手机不离身,恨不得有人把饭也给端来喂自己吃才好,若是有聚会,三五成群,唱歌喝酒吹吹牛,聊聊不那么靠谱的梦想和不知在哪的对象,等傍晚回家,华灯初上,望着天边的夕阳,突然间就有那么点青春的忧伤......然后呢,等歇够了,玩腻了,又想念起新鲜刺激的大学,豪情满怀,心就又动荡不安起来。少年啊,总是这么喜新厌旧,家乡不过是一个候鸟歇歇脚的地方,远不如中年人的避风港,老年人的归身处那样重要。
尤其是在北方,大同小异的城市,无甚差别的风景,到哪里都觉得莫名熟悉。归家不久后我便乘高铁去了西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沿途一成不变的耕地让我根本产生不了游子离家的哀愁。还是那样不甚整洁的街道,一样灰蒙蒙的天,关中平原的对于北方人来说并不难懂的方言,我几乎产生了一种仍在家乡的错乱感。身旁的西安同学感慨,出去四个月回来公交车站都变了,我的家乡呢,从小在外地上学,太久太久的离家让我对那个小小的县城既陌生又熟悉,然而,总归是陌生大于熟悉的。
家乡我已不很认得,远方又充满了诱惑,当大多数的我们所定义的家乡缩成十平米的屋,父母双亲,和一台电脑,一些食物的时候,当我们对远方不再充满恐惧的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那个给予我们抚慰,充满邻里之间欢声笑语,祥和安谧的家乡出现了模糊,它无法具化成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找不到它了。
还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专业不是太好,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和失落,焦躁和不安的情绪也在整个系蔓延。班内的助教是研究生学长,他用邮件群发了一封邮件,标题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没有什么说教的内容,不过是一些很灵性聪慧的句子,讲了他大一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光,和工作生活的琐事。读着读着我就安静下来了,你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内心充盈踏实的人,他的未来和人生他看得到摸得着,他喜欢乐意过这样的生活,看书喝茶听讲座,丰富丰富自己,和一样安静的读书人聊聊天,就这样过这一天天的日子。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家乡的感觉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地方,所以那些能让我们心灵安生养息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故乡,尽管会怀念那些吃了十几年跟身心无比契合的食物,尽管会怀念房檐上高挂的大红灯笼,尽管会怀念七大姑八大姨围坐一桌用高出常人八度的音调唠嗑,尽管会怀念父母粗糙的双手温热的触感,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奔向远方,然后在漂泊中不断寻找心灵的故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有一个叔叔曾告诉我,他的故土是如今中国最寒冷的镇子,曾经他以为自己一生都不会走出那个天寒地冻的小镇。当他第一次开车路过天安门的时候,手都在不停颤抖,不是因为他到了什么地方,而是他发现当年自己只能做梦,如今却已成为现实。如今的那个镇子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就和当年的他一样,告别了那片热土。
如果我们的心不曾安定,即使是那久违的家乡也难逃失落和迷茫,所以年轻的我们怀揣着动荡的心远离,然后不断回头。
如果没有远方,就没有故乡。
从此我的心撕裂成两半,一半揣在妈妈的怀里,一半带着它流浪......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商雨桐 返回专题首页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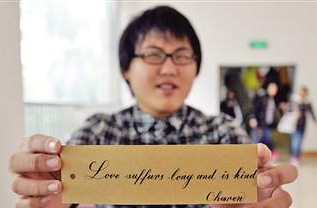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