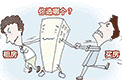我现在喜欢想一些“大事”,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想一些我解决不了的事情,比方说“乡愁”。现在这个词很流行,乡愁像床底下的土豆,不知不觉就会长芽。大家都说要留住乡愁,仿佛人人都成了李清照。李清照年过半百、美人迟暮的时候,在金华避难,愁肠百结,本想撑船游览一下,“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中国人变得这样多愁善感,原因是这个社会变化实在太快。城镇化像动车一样呼啸而来,让人猝不及防。昨天还在田里一脚水一脚泥,一下子变身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建筑工地上的搬运工、餐馆里的服务员、送水送气送快餐的伙计或者是公司里的白领,当然还有一些成了发廊和卡拉OK厅里的小姐。他们耳边还听到田里的青蛙叫,鼻孔里还留着水稻的清香,家乡就像一页还没有完全翻过去的日历。滋滋冒出的乡愁固然是对桑梓故里时过境迁的伤感,更是对自己青春不再的嗟叹。
当然,有些人脑洞开得更大一些,从中感受到一种文化式微的苍凉。据作家冯骥才调查,中国最近10年失去了90万个村落,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村落,2001年270万个,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他在全国政协会上说,“就现在开会的时候1天100个村落就没有了。”城镇化水漫金山一样淹没传统的村落,我不知道那些和他坐在一块开会的人是否有一种“包围圈越来越小”的感觉。其实这种情形并不需要太多想象力。每年春节过后博客微信上的回乡记述,基本都是一幅“乡村沦陷”的图景:萋萋荒草、断墙残壁、田园荒芜、村落空寂,青壮男女离乡背井,白发翁媪倚门而望……
从“文化”的角度,这的确是一幅末日图景。特别是当村落里的一些历史符号,比如名人故居、先贤遗址、古寺旧庙被人遗忘、日愈破败,那些小时候体验的习俗礼仪荡然无存,破落衰败变得可摸可触;加上市场经济下种种人情浇薄、你虞我诈,甚至于见死不救的现象,感觉世事纷扰,劳碌奔波,记忆中的乡村愈发变得景物怡人、风俗淳美,成为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正如陈寅恪评说沉水自尽的王国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大家都是农耕文明所化之人,乡愁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带来的苦痛。
这些沉浸乡愁、述说乡愁之人,尽管愁绪万千,但不会无可救药到像王国维先生那样,“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工业化、城镇化让人们享受着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成为无法抗拒的诱惑,越是这个时候,作为心灵守护者的文化,愈发凸显其保守属性,所以当他们返回乡间,难免合唱起乡村的挽歌。他们希望还能看到小河潺潺、炊烟袅袅,听到“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他们控诉城市的堵车、雾霾以及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情淡薄,感慨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城市的发展使农村也受到了污染,但这些从土地上拔足离开的人,只不过说说罢了,他们并不是厌倦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而是渴望过上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的寻梦人,因此断不会真的像他那样归隐终南、躬耕畎亩。
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当农人不再热爱土地”,说现在的农民对土地已经没有感情,任其撂荒长草,即使种庄稼也不再精耕细作,不再施放农家肥,而是大把地往里倒化肥,弄得土不成土,地不成地。文章写得诗意盎然、“满腔仇怨”,把土地比作读书人的书房,认为田园的贫瘠意味着心灵的贫瘠,土地的荒凉意味着心灵的荒凉。我感觉到在那份痛心疾首中,明显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矫情,而没有对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摔八瓣的怜悯。人与土地的关系的确变了,过去劳动与土地结合创造微薄的财富,现在它直接成为了商品。从文化角度这似乎是土地的“沦落”,但从经济的角度,它却是城镇化的必然。
工业化、城镇化堪称中国农耕文明之千年变局,工业文明的凯歌高奏,伴随的一定是农耕文明没落的挽歌。没有农村的“衰落”,就没有城市的繁荣。美国、法国、以色列等成为农业强国,一个前提就是传统农民的大量减少。冯骥才倒是很明白,认为要保住那些村落,根本的问题是要留住人。而这恰恰无法做到,因为它与工业化、城镇化背道而驰。农村人口的减少不仅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现象,更是进入这种“化境”的必然途径和手段,因此,村落普遍的“空壳化”是一个必然。
从某个角度,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历史宿命。虽然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但换一个角度,对于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何尝不是一种否极泰来,或者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呢?(照片取自网络)
(来源“狐眼碌碌”微信)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