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人民网独家发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
张旭东,198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 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学位,2005 年任美国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东亚系系主任。
再见张旭东,简单的衬衫、西裤,鼻梁上的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温文尔雅,最关键的,还是那么年轻。1965年出生于北京的张旭东,今年48岁了,可是,看上去和他的真实年龄少说也有 10 岁的差距。看上去年轻,资历却很老。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双料教授,并且担任东亚系主任的他,在学界早已声名卓著。
知道张旭东, 是因为本雅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旭东俨然已成了本雅明的中国代言人。由他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在1990年代的青年人中广为流传,一时间甚至成为了先锋知识分子的“识字课本”。
照例,和张旭东的对话还得从那本让他暴得大名的译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谈起。谈到这本书, 张旭东首先要感谢北大的图书馆。 “在80年代,”张旭东的眼前似乎闪过过往,“北大有个奇怪的传统,就是他们借书会去看后面的借书记录,看有谁借过这本书,找思想上的对话者。”
比如,找甘阳借过的书。虽然借书可以只写借书号不签名,但甘阳借书大概就像中央领导写“已阅”一样,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张旭东发现,他们借的书甘阳都借过,在北大,如果发现你借的几本书对方也借过,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人和你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就会打听这个人在哪儿,就会找上门去谈。这也是交友的一种方式。
大四刚开始的时候张旭东开始翻译本雅明。那时候他即将毕业,大家忙着分配、考研或者出国,很乱。毕业后他到新华社体育部担任记者,新华社要坐班,坐班的时候他就在翻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科长发现了很不高兴,不过北大学生自由散漫惯了,所以他也没有理会。1987 年年初,张旭东在新华社的资料室内把序言写完,写完之后交给这套书的编委会审稿,出版周期很长,1989 年6 月5日,他收到了2000元的稿费。已经在音乐学院工作的他骑着自行车从长安街上走过,到三联书店的财务部去取钱,这笔钱算是救了当时正缺钱的张旭东的急。
在翻译的过程中,1985 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名的西方马克斯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到北大来讲课。张旭东向詹姆逊请教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这让詹姆逊感到特别吃惊,他对中国学术界的印象就觉得这里应该是一张白纸,本雅明在美国也可以算是一个前沿的新热点,没想到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已经在译这本书,马上就对张旭东另眼相看。詹姆逊问他想不想去美国跟他读博士,但当时刚谈恋爱、女朋友在国内、文化热又如火如荼、有那么多朋友、当时是半个文学青年半个业余哲学家、觉得国内很不错的张旭东婉谢了詹姆逊的邀请。詹姆逊给人一个承诺就会记得,4 年之后,张旭东写信给詹姆逊,问他现在出国还行不行?
“他回了信,说还欢迎。”张旭东淡淡地说。
刘小枫推荐本雅明
留学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本雅明的?
张旭东:真正开始全面阅读本雅明是在1985 年,刘小枫将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书推荐给我。但之前我通过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对本雅明有所了解。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非常热的一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们与当时非常热的讨论,如异化问题、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有关联。年轻的一代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一定感兴趣,西方马克思主义吸引他们的是“西方”这两个字。那些学文学理论和哲学的年轻人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西方的社会、思想、历史问题都有很深的看法,在文学理论和美学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是从文化着手,再上升到分析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他们首先接触到的是文艺中的现代派文学。当时我们会喜欢阿多尔诺、布洛赫、本雅明、马尔库塞。其中,本雅明和阿多尔诺是比较偏文学的。和写作《否定的辩证法》同时具有哲学家的一面的阿多尔诺相比,本雅明则更为文学化。本雅明不会去研究黑格尔这样的纯粹哲学问题,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文化评论家、文学史家、自由撰稿人。
留学生:翻译的时候有困难吗?
张旭东:当时刘小枫是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副主编,他来找我,他觉得我在文学批评方面还比较擅长。之前我在翻译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 《世界图像的时代》,小枫对我说这些也很好,但是本雅明是你特别应该翻译的。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这本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应该感谢北大图书馆。那里太全了,一个本科生到图书馆里就能把原著给借出来。
我在上海上的中学,那里外语教育抓得比较紧,同学们也非常在意, 考大学的时候虽然英语成绩很好,但也不知道日后有什么用。在北大分在快班,但老师跟我说快班对你来说也太慢,他说你自己去读。我问怎么读?他让我去读原著。中学生初到大学,根本没有原著这个概念,他推荐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这是我毕生第一次借一本原版的英文小说,几天就读完了,觉得非常容易。此后我定期去图书馆借外文书。
北大图书馆相对于今天中国的财力、物力、全球化接轨的程度而言仍然非常超前。北大图书馆的编目非常完整, 除了特别前沿的, 你能想得到的书这里都有。
留学生:在北大的时候,当时是否有很多沙龙性质的小圈子,大家没事就聚在一块谈文学、讨论哲学问题,像海子他们那样?
张旭东:我认识海子,但交往不能算很多。中文系内部的人参加的沙龙不多,但是对广义上的现代派文艺感兴趣的还挺多。那时我和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博士生成了朋友,经常参加他们的讨论,虽然我是个 “外人” , 但这个圈子也不是什么秘密团体,定期不定期地会有一些学术讲座,很开放,北大的学生可以到处去听,这是北大的一个传统。中文系本身的教育当然很重要,但我的兴奋点不在这里。你也知道,中文系的教育到现在还是这样:古代文学、 现当代文学、 文学史、 古汉语、 党史……还比较古板。
另外中学时的一些比较“先知”的同学会给你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基本上把西方名著通读了一遍,包括李泽厚当时在谈的书,我们也在读。我们会非常关注什么样的书有出版,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出一本买一本,那种求知欲现在难以想像。当时的人都很单纯,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所有的兴奋都在思想世界之中,家庭和整个社会也支持你去阅读。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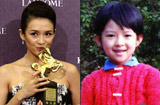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