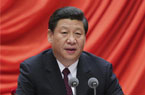1946年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學宿舍大樓前(照片由北京大學提供)
12月6日是侯仁之先生誕辰102周年紀念日,侯老終於沒有挺到這一天,一個月前離我們而去了。
今年8月,得到北京大學報告:醫院向侯老家屬發出病危通知。聽到這一消息,我放下手頭工作,急匆匆趕到了北京友誼醫院。主治醫生介紹說,侯老的心肺等器官已全部進入衰竭狀態,人已昏迷不醒,隨時有失去生命跡象的危險。我們聽完這一情況,穿上消毒服,直奔重症監護室侯老床前。我的嗓門大,大聲喊著:“侯老!侯老!我們來看您來了。侯老!侯老!”令人吃驚的是,侯老睜開了眼睛。他似乎熟悉我們這些老朋友的聲音,聽到了我們的喊聲,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安慰。從重症監護室出來,我把情況告訴了侯老的女兒、兒子、媳婦,大家都激動不已,因為這真是一個奇跡。其實這充分說明了侯老頑強的生命力。后來,侯先生的病情一度好轉,我們甚至樂觀地認為可以在12月6日為先生祝賀102歲的生日。未料天不假年,在我赴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前夕,侯先生在北京逝世,永遠離開了我們。
撫今追昔,20年來與侯老交談、向侯老請益的場景一幕幕浮現在眼前。他是和藹可親的長者,是聲名顯赫的學術泰斗,更是我們在教科文事業上的引路人和傳薪者,為中國的教育、科技、文化事業默默耕耘了一生。
慧眼卓識
中國申遺第一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68年來對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護是世界公認的重要成就,而侯仁之先生為中國的申遺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984年,侯先生應邀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時,從美國同行處了解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和頒布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侯先生曾專門撰文詳述這一經歷:在美國的建筑學界,很多位教授都十分關心我國古建筑和古遺跡的維修和保護工作,認為我們如能做好這一類的文物保護,那就是對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大貢獻。加州伯克利大學地理系斯坦伯格(Hilgard O.R.Sternberg)教授更直截了當地說:“中國的萬裡長城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不僅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也是屬於世界人民的。”他們都非常希望中國能盡快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侯先生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致力於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理念和實踐所感動,歸國后立即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起草了《建議我政府盡早參加提案》,並征得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三位政協委員同意且聯合簽名,在1985年4月召開的第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並獲通過。
1985年12月12日,我國成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並自1987年開始進行世界遺產申報工作。截至2013年6月,我國共有45個項目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位居世界第二,越來越多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受到我國各級各地政府的重視和保護。20余年來,隨著“世界遺產”這一國際性概念廣泛普及,越來越多的國人認識到文化和生態的價值,意識到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而其他國家的人民也通過這條渠道,對中國的文化傳承和風景名勝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今天,我們欣喜於中國世界遺產申報和保護工作蓬勃發展的同時,不能忘記侯仁之先生的“首倡之功”。
赤子情深
北京的守望者
侯仁之先生常說,他對北京“知之愈深,愛之彌堅”。自從20歲來到北京讀書起,他一生的事業與情感都與這座古城聯系在一起。侯老曾在一篇文章中憶起初入北京的感受:“既到北京而后,那數日之間的觀感,又好像忽然投身於一個傳統的、有形的歷史文化的洪流中,手觸目視無不渲染鮮明濃厚的歷史色彩,一呼一吸都感覺到這古城文化空氣蘊藉的醇郁……這一切所代表的,正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歷史文化的‘訴諸力’。它不但訴諸於我的感官,而且訴諸於我的心靈,我好像忽然把握到關於‘過去’的一種靈感,它的根基深入地中。這實在是我少年時代所接受的最偉大的一課歷史教育,是我平生所難忘懷的。”
年少時激發的情感貫穿了侯先生整個學術人生。他在北京城的起源和城址選擇、歷代水源的開辟、城址的變遷沿革、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和規劃設計等方面所做的大量研究一直為人稱道﹔更讓人感動的是,侯老一直到晚年仍為古城的保護而奔走。
上世紀80年代,侯先生曾撰文《盧溝橋與北京城》,詳述盧溝橋與北京城的淵源。他認為,盧溝橋800年的歷史與北京城可謂是血肉相連,它不僅顯示了古代人民卓越的工程技術,也是北京城原始聚落的誕生之地,亦被馬可·波羅贊揚並揚名歐洲,而近代以來,它又見証了日軍侵華的鐵蹄,標志著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全民族抗戰的起點。當侯先生得知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盧溝橋頻繁行車而導致橋體面臨損毀危機,他馬上撰文呼吁“保護盧溝橋刻不容緩”,認為“盧溝橋所面臨的問題,雖然發生在首都,影響卻在全國,甚至在全世界”。
在侯老的大聲疾呼和奔走下,盧溝橋很快得到了妥善的保護和整修,后來還被列為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
1993年,北京西客站破土動工,選址就在蓮花池畔。當時的蓮花池已經干涸,有人提議直接把北京西站建在蓮花池原址上,既可以節省搬遷的人力物力,還能利用凹陷的地形。侯先生提出明確的反對意見,強調“先有蓮花池,后有北京城”,“蓮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頭”。這個意見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蓮花池原址被保留了下來。在北京西站建設期間,侯老一直惦記著蓮花池,還和夫人張瑋瑛老師親自去了一趟施工現場。那時候主體工程雖然完成,但是還沒有裝電梯,當兩位老人一步步攙扶走上樓梯,看到的是干涸的蓮花池底,裡面堆放了建筑材料。侯先生憂心忡忡,回去又寫了《蓮花池畔再造京門》,建議開發蓮花池的水源,恢復其原貌。
1998年4月28日下午,87歲的侯先生應邀前往北京市委去作報告介紹北京城市的歷史。他在題為《從蓮花池到后門橋》的報告中講到:“由於蓮花池的存在,影響到一個古代城市一步步成長,最后擴建為金朝的中都城。這就是北京建都的開始。因此可以說北京城的成長和蓮花池的關系至關重要……現在北京開發水利工程,我殷切希望能夠把蓮花池盡可能地加以恢復。”先生的報告受到北京的高度重視,他的建議也被正式採納。兩個月后,蓮花池恢復改造工程正式啟動﹔緊接著,侯先生報告中提議的后門橋修繕計劃也開始啟動。后門橋所在地是元大都城市規劃的起點,沒有它就沒有北京城市南北的中軸線。侯先生建議把什剎海的水引過后門橋,恢復后門橋下河道的景觀,使歷史上中軸線設計的起點重新煥發光彩。2000年12月21日,蓮花池和后門橋遺址舉行修復儀式時,侯先生雖然行動不便,但仍堅持坐著輪椅前去參加。
坐落在北京城西北角的“三山五園”,亦是侯先生一生的牽挂。從讀大學起,他的足跡遍及頤和園、西山、圓明園。侯先生曾風趣地講過,“在燕京大學我等於是上了兩個大學:一個是正規的六日制大學——就是燕京大學﹔還有一個一日制的大學——我叫他‘圓明園大學’。”上世紀50年代初,侯先生擔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時,通過對北京西北郊新定文化教育區的地理條件和發展過程的實地考察,寫了《北京海澱附近地形、水道與聚落》等文章,為新區的規劃提供參考。侯老到了晚年,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再做長途考察,他的關注點便又回到當年的學術出發地,圍繞海澱和燕園做了“未名湖溯源”、“海澱鎮與北京城”等研究。1995年左右,侯先生眼見城市建設的高速發展恐對生態環境和歷史壞境造成一定的破壞和威脅,於是提出,要採取措施,把頤和園東側面積數千畝的地區(即萬柳地區)保護起來並予以綠化,成為北京的一個大“綠肺”。北京市接受了侯老的建議,“萬柳工程”成為北京綠化隔離帶建設規劃面積最大的項目之一。
一直到侯老95歲高齡時,他念念不忘的,還是京城西北郊歷史環境的保護。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應當從兩個方面考慮對環境的保護:一是海澱和西北部的香山一帶,是歷史上北京重要的風景名勝區,考慮到其對現代北京生態的重要作用,要重視生態走廊的保護與建設。另一個是在海澱附近,有圓明園和頤和園等名園的存在,頤和園還是世界文化遺產,要保護好遺產的本體及其周圍的環境,控制建筑高度,防止污染,努力營造良好的生態與文化環境。2012年6月,北京把推動海澱三山五園歷史文化景區建設列為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
倘若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忽視了文化傳承,往往會使我們誤入喧囂和泥淖。侯先生仿佛一位睿智的先哲,在崎嶇和迷霧中引領我們上下求索。感謝侯先生等前輩的努力,沒有他們的執著,我們不知會失去多少歷史的遺珍。
哲人其萎,文字不朽
苦難中的作品《北平歷史地理》
12月6日也是先生博士論文《北平歷史地理》出版首發的日子。
2010年8月,侯先生夫人張瑋瑛老師因為侯老的病情而焦慮萬分,突發腦梗塞昏迷不醒,住在北醫三院。
我和張偉瑛師母也非常熟悉,過去每次探望侯老,師母總是端茶倒水,不離侯老左右,談笑風生,為我研究司徒雷登與燕大提出了許多卓有見地的建議。侯老已經很長時間臥床不起,師母也是為照顧侯老而著急病倒。一聽這個消息,我馬上趕到了北醫三院。那時候侯老住在北大校醫院,師母住在北醫三院,他們的子女也為看護老人而在兩個醫院奔波。幸運的是,師母被搶救回來,但不能言語。我為侯老百歲生日祝壽的《靜水流深 星斗其人》一文發表之后,侯老女兒侯馥興大姐特意把文章念給師母聽。大姐告訴我,師母聽后露出笑容。我相信,老師與師母雖然不住一個醫院,心靈卻是永遠相通的。
也正是在我這次去探望師母的時候,得知侯老上個世紀40年代末於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時的博士論文《北平歷史地理》還一直未有中文版問世。歷史地理學界的專家一致認為,這部著作無論是在侯先生個人的學術發展歷程中,還是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標志作用,至今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仍具有重要意義,堪稱經典。外研社第一時間聯系侯老的家人取得授權,聯系北京大學鄧輝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申雨平教授等進行翻譯。經過3年多的努力,這部凝聚了侯先生學術智慧的作品就要面世了,這是令人激動的事情。侯馥興大姐告訴我,今年9月24日,這部著作的試讀本被送進病房,伴隨了侯老人生最后的跋涉。外研社的編輯特地選用了侯先生手繪的北平古城圖作為封面,封面特地選用的朱紅底色,也正是紫禁城宮牆的顏色。
馥興大姐還告訴我,侯先生這本著作的腹稿,是1941年他被關押在日本陸軍監獄時構思的。這本寫在身陷囹圄、國家危亡時刻的著作,不僅是苦難中的習作,亦是侯老30歲時的明志之作。我又想起侯老1944年寫給大學畢業生的寄語:“一個青年能在30歲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獻身的事業,努力培養他的士節,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國家和社會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侯仁之先生用他元氣淋漓的學術人生,獻身於祖國的教育、科技、文化事業,使得國家、社會乃至今天的青年學生都享受著他的余蔭。
謹以此文紀念侯仁之先生。(郝平)
(本文作者為教育部副部長——編者注)
(來源:中國青年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