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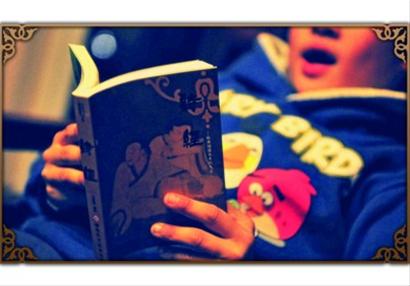


上圖:2013年1月,一名在外省私塾學校就讀的孩子返家后,向記者介紹自己的教材。陳征 攝
這是一群每日讀著經典古文成長的孩子,通過一種在大多數人看來比較“小眾”的教育方式。
學生中,有的是自願而來,有的是被家長“坑”來,有的開始不適應,之后卻再也不願離開。
小至5歲,大至20多歲﹔短的才讀幾個月,長的輾轉多個學堂讀經,已有七八年。
不接觸手機、iPad等電子設備﹔力求重現古代私塾教育的精髓,每日重復誦經,直到完全記住。
在外人看來,他們也許會變得“閉塞”、“迂腐”,有孩子卻自己說“幸福感”由心而生。
遂昌王財貴經典學校位於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為9年全日制民辦特色學校,已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多位學子。
關於辦學宗旨,學校網頁上寫道:“我們現在實行經典教育,和一般體制內的學校教育相比,是一種開拓與創新﹔然而與自古幾千年來,文化傳承人才培養的方式相比,其實又是一種回歸。”
電話裡,當我們提出來學校看看時,董事長趙升君想了想,說:“來吧,來看看!剛好這幾天學生返校,來和家長、孩子聊聊,否則外界總以為我們這裡很怪。”
家長篇
“我要給兒子做一個對未來不可預測的決定,這真的很難。”
“這算不算是場賭博呢?”張宇扒完最后一口飯,若有所思地拋出這句。
我們猜,這是對我們之前一個問題的補充回答。
表面上,他是被採訪家長中最不管孩子的一個——別的家長都和孩子在一塊兒吃,他倒無所謂地和女兒分開活動,任她和小朋友嬉戲打鬧。
他告訴我9歲的女兒已背完《論語》、《孟子》、《易經》、《詩經》,看到孩子們齊齊吟誦詩經的視頻,由衷感動﹔
說到3年間,女兒發生了很多變化:“原本很膽小,現在很活潑,敢在生人面前說話。”但也笑著說在學校很守規矩,到家后就“打回原形”﹔
“那之后,還打算讓孩子回到公立學校繼續讀嗎?”
“隨她吧,先讀下去,之后讓她自己選擇。”
在這裡讀經的孩子,除了短期讀暑期班的,都意味著放棄了同期的普通體制學校的教學模式。
“如果覺得經典好,為什麼不在課余讀,比如周末?”
“我希望她接受系統讀經教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希望她學最好的。”
但一頓飯后,他還是忍不住表達了開頭的那種糾結。
這種糾結和對未知的焦慮感,或強烈或隱約地存在於大部分家長的心中。毛敏也是其中一位。
她陪著11歲的兒子佳佳上學。此前,佳佳在這讀過暑期班﹔而這次,她與兒子下定決心在這裡讀上兩年,初中再回歸“體制”。
她仍然真切記得在給兒子辦轉學手續時,當地小學的老師苦口婆心地勸她:“你為什麼拿孩子做試驗品。”
“沒有人想把孩子當試驗品,”她說,“給兒子做一個對未來不可預測的決定,這真的很難。”
她堅信讀經對孩子有好處,但一種糾結於心:孩子還是應該回體制內學校上初中,但學業在兩年后還能跟得上嗎?
她反復詢問其他人家孩子的選擇和去向,得到的信息五花八門。
有人讀了幾年回歸 “體制內”。“一個小孩有尿床的毛病,自信心不足。結果在這裡讀了兩年半,自信心回來了,后來還做了語文課代表!”“山東的一個小姑娘讀了8年。16周歲還不到,准備在家自學考大學。她去學琵琶,上一節課等於別人上三節課的效果。”
……
這些,都是讓她感到有信心的例証。
還有人選擇“一條道走到黑”,打算進“書院”——類似讀經者的大學。
還有人無所謂孩子的選擇。“考不考大學並不重要,”他們認為,0到13歲是人一生中記憶的黃金時間,“孩子應該在最好的時間讀最好的書,鍛煉記憶的能力,學習文化的精華。這些是中國人讀了幾千年的書,你說會不好嗎?”
當然,也有人跟風。覺得孩子在體制內學校學習狀態不好,希望這裡能找到另一條路。
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選擇的理由。
總之,綜合考慮,毛敏一家決定——要讀!
除了糾結前途,他們還需要履行“家長公約”——在校期間沒有星期天﹔每個月隻能打一次電話﹔非放假時間家長不能來校看望孩子﹔學生在校期間不能帶零食、零錢、手機﹔每年除寒暑假合計45天外,其余時間都是在校照常學習……
同時,還有相對艱苦的生活硬件。十張床鋪一間房,約五六人一間﹔一層樓共用一個盥洗室,也不能每天洗澡……
對每位疼愛兒女的家長來說,這又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開學前一天晚上,毛敏問佳佳:“后悔嗎?后悔的話還來得及,媽媽可以幫你請兩天假!”
一位家長用“草原上的狼”和“動物園裡的狼”說服自己和女兒——“草原比動物園條件艱苦得多,但難道不是草原上的狼更具生命力嗎?”
另一位家長在信中回憶與兒子分別的場景——
“包的車來了,媽媽要走了,想與你告別,你與幾個同學用稚嫩的童聲合唱 《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淚水直流。
教師篇
“人文教育,人在前、才在后。好的東西應該盡早讓孩子知道,比知識更重要。”
“這個學校的創立,不是血淚史,也是辛酸史了。”校長周?轄讀經多年,曾嘗試辦過私塾班,結果需求太旺,一個班很快變成了三個班,最終她決定創辦一所讀經學校。私塾班易辦,成立學校可並非易事。周?轄四處奔走幾經輾轉,最后在遂昌拿到了辦學資質。學校目前的所在地,也是當地一所中學撤並后留下的校舍。
學校2009年響起了讀書聲,全稱為遂昌王財貴經典學校。王財貴是誰,為何冠以他的名字?
王財貴是台灣台中師范大學的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入室弟子。1994年,他在台灣發起了“兒童誦讀經典”的教育運動。
趙升君說,王財貴曾多次來學校參觀,也同意用他的名字來推廣讀經。
推廣讀經之路並不平坦。
首先就是資質。類似的讀經私塾曾相繼被關停便是因為沒有獲得辦學資質。
現在學校已獲批文。而取得批文的代價是,每年級都要完成相應的教學大綱目標,其中包括數學。
有家長提出,讀經可以佔主要,但數理的基礎內容還是不能不教。
學校原本的理由是:根據王財貴的教育理念,數理的教育應在生活中學,不必急於求成。數理是以理解為准,而理解深具個別性,應採用自學的方式,而不是統一進度,甚至可以“擱置”——專心致力於讀經及閱讀,盡力增長德性、定力及聰明﹔13歲以后,花兩三個月的時間專心學完體制內6年全部數理課程。
且不論“突擊學數理”的想法是否科學可行,這還是沒能說服部分家長。上月,學校剛剛組建起家長委員會,商討了一系列問題:是否應該加入數學科目的學習,理化的基礎知識是否傳授,眼保健操該不該有……
學校沒有固執己見,對於“家委會”最終的決議,他們基本都採納了。
“其實對於我們的孩子,小學程度的數學真的不是問題。”趙升君說。
有與眾不同的理念,沒有讓人敬佩的老師,家長不一定選擇這裡。
十幾年歷任中小學教師、教導主任、副校長,李寧仍辭去公職,專心教學生讀經。她覺得做讀經老師是“佔了便宜”,因為在帶孩子讀經的同時,順便也把自己沒讀過的經典一並讀了。
李寧曾寫過一段與孩子們讀書的場景:一天陽光極好,她帶11位孩子在教室外讀經。恰好千年古樟的枝葉綿綿密密地伸張開來,讓陽光不再那樣肆無忌憚。樹葉間的光影洒在翻開的書上斑斑駁駁,讓讀書變得格外有味道……
讀經也有考核,一般月中和月末會分別檢查背誦。每到這時,年紀大的孩子愁眉苦臉,小孩子則是歡天喜地,一個個爭前恐后搶著去背。李寧故作嚴肅告誡:“誰好好讀書,就給誰第一個背!”孩子們為了爭取能夠早早檢查背書,更是異常積極地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水環繞,輕聲優雅。此讀經,不亦說乎。”一位青年教師寫道。
曹利平30歲,來學校教書兩年了。剛從師范學校畢業時,他到處打工,把錢放在第一位,但在這裡,他感到心平如鏡,“自己的游魂在這裡終於得到了安放”。
有一年放假回去,發小開著私家車來接他:“你看你,去那個學校,房也沒買,家裡房價都漲啦!”曹利平心裡又起波瀾,但他克制住了自己。
開在半道,他突然提議:“我們干脆把車停在這裡,像小時候那樣跑回家去,看誰跑得過誰,怎麼樣?”
發小不理他:“有車了,干嗎還走啊?”
曹利平自己感嘆:“人既然長了腳,就是用來走的啊。其實我們的人生,買了太多的東西,但是又有哪一樣能夠帶到墳墓裡去呢?”
他說經典教學生如何做人,也在教自己如何做人。
學生越來越多了。最開始,學校隻有24位學生,現在有200多人。但這個數字並不穩定。有的家長不滿意校舍,有的家庭內部對讀經意見不一,孩子入學又退學的情況並不罕見。學校在招生要求上特意標明“家庭成員理解支持”。
老師的數量也翻了好幾倍,大多數老師各負責一個班,讀經、體育、寫字全都教,還有教授形意拳的老師,以及專門負責孩子起居與健康的生活老師。
學校也慢慢五臟齊全:外宣部、教導處、總務處、生活健康處、政教處各司其職,最近還規劃了生活部。
周?轄希望學校能安靜成長:“我們的學校只是一棵幼苗,它經不起任何風吹雨打。”
學子篇
“吟誦不是給別人聽的,是給自己聽的。”
因剛開學,規矩還沒開始執行,孩子們顯得分外“放縱”﹔校園裡,家長們或站或坐,愛憐地看著陽光中嬉戲的兒女。
近處是千年古樟繁茂的枝葉,遠一點是連綿的灰色房子、錯落有致的屋頂、煙囪,再遠處是青山綠水,連綿的山巒聳入雲霄,雲如煙如霧環繞……“如果學校可以每天洗澡,簡直就是天堂了。”一位剛來學校一天的女孩對媽媽說。
《梅花三弄》的旋律響起,是上課鈴聲。四樓的一間教室已經開始了對上學期課程的復習。
一節課70分鐘。每個人選擇一個片段一一吟誦給老師聽。老師鼓勵:“吟誦不是給別人聽的,是給自己聽的。”
學校從去年開始全面推行吟誦,這被專家一致認為是讀經最原汁原味的方法。抑揚頓挫而特別的吟誦一遍遍地響徹教室,別人吟誦的時候,不少學生也跟著搖頭晃腦地一起背。
“這種旋律,需要學嗎?”
“很好學。”身邊的女孩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旋律,關鍵是不能‘倒字’”。
天宇要站起來吟誦,他的聲音很放得開,與窗外風吹過竹林時沙沙的聲音彼此應和。
天宇是在原來的學校讀完高一來的,短短兩年半,已經背誦十多萬字的經典。他說自己原來“成績不是很好,內心感覺空虛,不喜歡看書”,但現在喜歡看書了。天宇的爸爸是商人。關於教育、思考,他直言“沒什麼好說的,我本就是個生意人,沒讀過幾年書”。但最近兒子的一番話卻讓他震動不小:“爸,不要老是談錢。重要的不是賺錢,是把人做好。”
這位16歲的男孩在心得裡這樣寫道:“我可以沒有錢,可以沒有地位,可以沒有大事業做,但不可以沒有幸福之感。最近的我會感到掃地也是一種幸福。掃過的是落葉和塵埃,換來的是下一刻的清新與明亮。”
並不是所有孩子都能有如此感悟。
“媽媽,可不可以以后別提我在讀經典?”在又一次被人追問在“那個學校”的感受后,11歲的小雅小心翼翼地向楊慧提出了請求。
沒有任何人贊同楊慧送女兒來讀經學校,她原本以為壓力隻在自己身上,沒想到孩子同樣有壓力。
2009年春節,讀經剛滿一學期,小雅幾乎被所有的親友問了個遍——“那裡都學什麼呀?”“在那裡快樂嗎?”
小雅低著頭,嘟囔著“還行吧”。
其實,小雅早已習慣了讀經學校的模式。私下裡,她和媽媽開心地描述過在學校裡的時光:把《哈利波特》全集看完了,還交了幾位好朋友。
“我被我爸媽坑了。”角落裡一位男孩大大咧咧地說。13歲的小白是被爸媽以“這裡不用寫作業”為由騙來的,但在這並沒有改變其調皮搗蛋的性格。有一次在課堂上,他和坐教室對角線的男孩玩 “漂流瓶”,寫好紙條后裝在瓶子裡扔過去,對方答復完再塞到瓶子裡扔回來。一來一往,直到他扔過頭命中帶班老師的肚子……
他對讀經態度的轉變不是來自老師,而是同班同學舒宜。
舒宜已18歲,讀經5年,算是“元老”了,也是很多家長心目中的“模范”。待人彬彬有禮,吃完午飯后,餐盤和飯碗中不留一粒米、一片菜葉。
在小白上課不聽的時候,她抓著小白的手,指在書上,一字一句地教他念。小白 “一下子就被感動了”,第一次感受到認真讀經的快樂。
舒宜說,在學校讀經,最不一樣的是來自於年齡不相同的同學們。既是同學,卻又是兄弟姐妹。在她最有困惑的時候,也是“哥哥”、“姐姐”和老師們引導、幫助了她。
不僅是幫助,孩子間的治愈也很有效。
“哇哇哇,我要爸爸……”一位五六歲的男孩站在場地中央,他的爸爸已經走了。有大孩子走過去拿玩具逗他,看不起作用,便也都走開了。
哭聲漸弱。他扭頭四處張望,看到教室裡別的孩子玩得正歡,自己擦擦鼻涕,不哭了……
思考篇
“讀經,到底會對人的一生有怎樣的影響?”
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家長希望探索一種因材施教的個性化教育。這已是一種客觀現實、客觀需求。
但也有家長憂慮:“誰都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讀經,到底會對人的一生有怎樣的影響?”
經典是好東西,但什麼時候給,什麼樣的孩子給到什麼程度?
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經歷千年發展,其中確有其可取之處,但現代社會離私塾時代相去甚遠,孩子們除了讀經之外,其他課程如何處理?
這些問題,沒有人能給答案。
“我不想說我們的教育很完美,但至少是多元教育中的一種存在。”周?轄說。
多元化的教育可以彼此借鑒。當經典學校在碰撞中改變時,體制內的學校或許也能從中得到啟發。
“沒有一種教育是萬能的。”教師陳鐵波在心得中寫道。
教育,注定了是一場多樣化的探索。
(文中家長與學生均為化名)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