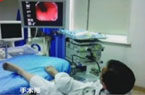因为代理海南省三亚市一农场83名职工相关农场经营权案子,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两审均判败诉,上月底,59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景一,带领职工到三亚市信访局门前跪访。对此,刘景一二十多年前的学生、浙江律师钟锦化在微博中亦称:我一直强烈反对因讨不到公平公正而动不动就下跪请愿的做法,这更不是一个法律人应该提倡的做法。(《南方都市报》1月20日)
指责刘景一的跪访是容易的:堂堂法学教授竟用如此反法治的方式表达诉求,这是多么“恶劣”的示范啊?连法学教授都不信仰法律,又怎么能引导普通民众树立起法治思维呢?固然,不被信仰的法律形同虚设,这样的道理哪怕一个普通的法律本科生都耳熟能详。可为什么法学教授也如此行事?
刘景一的“反法治行为”是在穷尽法律途径仍然维权无望后的无奈之举,他本人也非常清楚这样的行为和个体的尊严、自己的身份之间的冲突,但正如他本人所言,“在跪的那一刻内心也很挣扎,但想想,我个人膝下的黄金和83人的公平正义谁轻谁重,这种做法可能是让他们获救的唯一希望,如果不那么做,83人一分钱得不到。”
这其实不是刘景一一个人的尴尬,而是不少认认真真走完法律程序者共同的无奈。在去年广东“两会”上,当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刚谈到要引导群众信法不信访时,同组的省人大代表林春涛当面向黄业斌反映了一个问题,并将有关信访材料交到黄业斌手上,林春涛的解释是,“我也是代表,实在没办法了,法律程序都走了。”
不管是法学教授的“下跪上访”,还是人大代表“两会现场上访”,悲哀的都不是当事人的身份,而是法律的权威。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究竟是法律最有权威还是权力最有权威,不是看纸面上的言辞,而是实际运作的逻辑。如果权力总是高于法律,那么法律甚至不被最该信仰它的人所信仰,就会成为一种看似相当尴尬却绝对符合实际理性的现象。
更悲哀的是,“有身份”的人不管其行为多么“不符合身份”,至少他们的诉求能表达出去,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听到,起码不至于成为“沉没的声音”。可以想象,在艰辛的维权过程中,还有多少选择“下跪上访”的当事人,在长时间的“下跪”中,收获的还是诉求无从表达的尴尬和无奈?有多少人在走完所有法律程序之后,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向市委书记当面递交信访材料?
原本非常正常的维权行为,竟然需要那么多“附加条件”才能顺利表达出来,这该多么不正常。当维权越来越需要“比拼创意”时,说明我们的社会麻木感在与日俱增,对悲情的“免疫力”正在不断增强,这也意味着维权成功的概率越来越低。正如成功策划“农民工模拟外交部发言人讨薪视频”的奇姓男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的,“这事儿说起来挺悲哀的。黑锦和手里拿着判决书呢,那是什么,那是国家的法律啊,但是一直没有生效,你让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好多次都说想采取极端手段,但是这样的事社会上太多了,社会都麻木了。我做这行久了,点子真的越来越不好想,这是挺无奈的一件事。”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