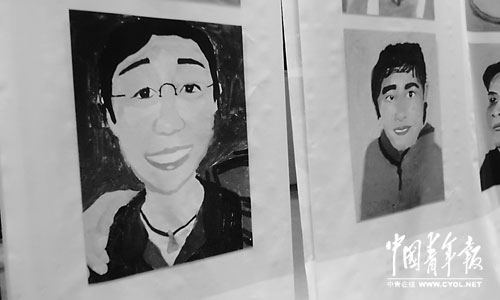
4月2日,為時一個月的名為“當我遇見你”世界兒童融合藝術大展結束,圖為該展展出的一位自閉症兒童的繪畫作品。此次展覽由中國科學技術館、人民政協報、中國青少年宮協會等單位共同主辦。本報記者 樊未晨攝
自閉症兒童數量快速增長
三月底的北京,春天還沒有來。北京21世紀實驗幼兒園在朝陽區的一個分園內,正在上一堂普通的美術課,孩子們被要求畫出春天的花朵,一張張色彩綻放的白紙上畫滿了孩子們對春天的期待。
教室中七歲的東東(化名)是個很秀氣的男孩子,睫毛長長的,像兩扇小翅膀。與別人的畫紙不同,他握住一隻藍色水彩筆,將面前的白紙戳滿狹長的點子。
東東患有輕度孤獨症。
孤獨症,又稱自閉症或孤獨性障礙等,是廣泛性發育障礙。雖然人類還無法獲知病因,但是,它卻給病兒及病兒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痛苦。更令人無奈的是,自閉症兒童的數量正在快速增長。
為了提高人們對自閉症和相關研究與診斷以及自閉症患者的關注,聯合國把每年的4月2日定為“世界自閉症日”。
“曾經,它的出現率為千分之一左右。”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鄧猛介紹,但是近些年這個比例在快速地提高,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一份幾年前的研究顯示,每150人中有1人患有自閉症。
我國的自閉症患者數量也在不斷升高,據全國殘疾人普查情況統計,兒童自閉症已佔我國精神殘疾首位,中國殘聯的統計顯示,2012年,我國僅在各類機構學習的孤獨症兒童就有1.1萬人。鄧猛教授介紹,有研究甚至得出1/80的數字,即每80個人中就有一個是自閉症患者。
一年級的浩明在海澱區一所小學上學,之前他一直被公認為是個淘氣的孩子,但是上學以后,他才發現自己那點兒“小淘氣”真的不算什麼,班上有個更“特別”的孩子,他會上著上著課就在教室裡亂轉,他也會在某個時候突然大怒起來,不得已,老師會經常請他媽媽來“陪讀”。后來,他才知道這個同學患有自閉症。
“世界自閉症日”前夕,本報記者走訪了幾家幼兒園和小學,這群看似特殊的孩子就生活在普通孩子身邊。
特殊進入普通,道路並不簡單
今年一月,北京市教委出台了文件,要求普通學校必須免試接納就近隨班就讀的特殊孩子。
雖然我們無法准確獲知自閉症的成因,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越早干預對自閉症的治療越有好處。讓患有自閉症的孩子進入普通學校就讀,既能保障他們受教育的權益,也能幫助他們將來更好地融入社會,自食其力,同時也能更好地挖掘他們特殊的潛力。
不少研究表明,很多自閉症兒童雖然在某些學習上存在困難,但是卻在機械記憶或空間技巧等方面有著特殊的能力。
北京市朝陽區新源西裡小學特教部主任朱振雲現在還記得,她曾經教過的一個自閉症的孩子——大鵬(化名),“三位數乘四位數他直接就能算出來,有時候比計算器算得還快呢。”朱主任說的這個孩子,現在已經順利考入了一所普通中學。
雖然社會目前有共識:應該讓自閉症的孩子進入普通學校就讀,但是,簡單的隨班就讀會因為普通老師不具備相應的特教知識和經驗而無法對這些孩子進行更有效的教育,同時也會給日常教學帶來很多困擾。
浩明的爸爸說:“我們挺矛盾的,班裡那個‘特殊’的孩子經常攪得其他人沒法上課。”最讓他擔心的是,自己的兒子的某些行為好像是跟那個孩子學的。
這是所有自閉症孩子在普通學校上學都可能會面臨的問題。
大鵬剛到新源西裡小學時,非常躁動,上課時會在教室裡不停地動。朱振雲介紹,很多剛入學的自閉症孩子在教室裡根本待不住,朱振雲記得一個自閉症的孩子溜達到傳達室,傳達室的老師養了一盆金魚,這個孩子就從裡面撈出一條,然后面無表情地一捏,小金魚就死了,然后再捏一條、再捏一條,直到所有的金魚都被捏死。
“絕大多數自閉症孩子進入學校時都有嚴重的情緒問題,這時候學校的首要任務就是疏解他們的情緒。”朱振雲主任說。
在新源西裡小學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教室,裡面擺放著一個沙盤,四周的櫃子裡擺放著各種小玩具,比如各種人物形象、各種汽車、各種武器、漂亮的公主、色彩鮮艷的水果……這是一種國際上很流行的心理治療方法,通過孩子在沙盤上擺放物品的情況,可以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類似的教室還有幾間,都是用來尋找孩子們的心理問題,同時有針對性地對他們進行疏解和簡單矯正。
新源西裡小學實施的並不是簡單的隨班就讀。這裡既有普通班又有特教班,實施的是融合教育。
自閉症的孩子來后,首先是在特殊班學習,主要的任務就是疏解情緒,大概會用一年左右的時間,“孩子的情緒好了,他跟他人的關系自然就會改善,這個時候再慢慢地讓他們調整自己,先是做到可以了解別人的情緒,進而了解別人的感受,慢慢再學會與別人合作。當這些孩子具有這些能力以后,我們才開始嘗試讓他們進入普通班學習。”朱振雲說。孩子們首先從音樂、美術等相對輕鬆的課程開始學起,逐漸向主科過渡。
而當這些孩子進入普通班學習時,情緒上出現任何問題都會有專門的特教老師及時幫他們進行調整。
其實,隨班就讀是目前我國70%輕微殘障孩子的學習之路,但是,能擁有像新源西裡小學這樣配備的學校並不多。
記者在朱振雲辦公室內的一個多小時時間裡,相繼有三四個咨詢電話,都是那些在普通學校隨班就讀的孩子家長打來的。
朱振雲介紹,每年到他們學校來報名的特殊孩子有七八十人,其中患孤獨症的孩子超過一半,有時能達到60人,但是以他們學校目前的條件每年隻能收7∼8名特殊孩子,孤獨症也就隻有一半。
據了解,在北京,像新源西裡小學這樣完全擁有融合教育條件並且每年都在招生的學校並不多。
師資、資金是最大的困擾
“每年招生的時候,看著那麼多孩子和家長,真的想多收幾個,可是我們做不到呀!”朱振雲說。
進行這種擁有資源教室和專門的特教老師的融合教育,需要的不僅僅是觀念,同時還要有人力和財力的支持。
“特教工作一直留不住人。”東東所在的21世紀實驗幼兒園的劉園長說。這不是個例,新源西裡小學同樣面臨著老師不夠的問題。該校有9個特教班,每個特教班有七八名學生,同樣也要配備班主任,但是學校並沒有特教老師的編制,師資的匱乏程度可想而知。
據鄧猛教授介紹,即使是在特殊教育發達的北京、上海,特教老師也多由普通老師兼任,僅受過簡單的培訓。具有特殊教育專業背景的老師極度缺乏,也大多分布在各個特殊學校。
“No money ,no face, no hope(沒錢、沒面子、沒希望)。”鄧教授無奈地調侃道,薪酬與勞動付出完全不匹配,社會偏見大,職稱評定受限制,發展空間又不大,自然不會有年輕人來做。
很多老師是靠著良心在堅持的。
小溪老師是21世紀實驗幼兒園的一位特教老師,她記得一次暑假結束,自己回到學校,遠遠地看到大奔(化名)從操場的另外一頭向她跑過來,樂觀、外向的小溪眼淚扑簌簌地掉下來。大奔是她教的一個自閉症孩子,這個孩子跟其他人很少有感情交流,即使是日常的溝通,他也很少有回應。“大奔奔向我的那一刻,我知道都值了,我知道他是有那麼一點點、一點點在乎我了。”她說。
很多老師是靠著這些內心深處最柔軟的東西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但是,如果沒有與之匹配的政策傾斜和保証,特教老師的隊伍始終是不穩定的。
經驗缺乏是最大的挑戰。近年隨著孕前篩查的發展,罹患唐氏綜合症、腦癱的孩子相對少了,但患孤獨症等精神障礙的孩子變多,因此,即便是特殊學校的老師,也經常不知道該如何教育這樣的小孩。
資金更是大問題。據了解,盡管已有所補助,一些私立幼兒園的特殊教育收費遠遠超過一般家庭能承受的范圍。像新源西裡小學這樣屬於義務教育的公立機構,盡管能減免特殊孩子的費用,但是在師資建設方面,也沒有專門針對特殊教育的補助,隻有北京市教委和殘聯的一些專項補助,並不穩定。一些老師介紹,雖然國家對特教很關注,但是很多資金都投向了專門的特教學校,向新源西裡小學這樣的普通學校很大程度上都隻能靠自籌。
“這不是施舍,是特殊孩子本來就有的權利。他們本就屬於我們的世界。”鄧猛教授說。
當特殊孩子進入普通世界,帶來的是財富
一直以來健全人都是用同情之心來看待特殊人群的,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以幫助他們為前提的,但是當這些特殊的孩子真的進入到普通孩子世界的時候,他們也帶給普通孩子一筆巨大的財富。
“首先是接納和包容。”不少從事該項事業的人士介紹。
起初,人們會認為這些特殊孩子或許會遇到普通孩子的嘲笑、歧視或者是簡單的排斥,但事實相反。
朱振雲還記得十幾年前的學生曉瑞(化名)。“那是個挺厲害的小姑娘,”朱振雲介紹,但是當曉瑞見到比她高一級的腦癱孩子彤彤(化名)時就化成了溫柔的棉花糖。小小的她費勁地摸著比自己高一截兒、大幾歲的彤彤的腦袋,安撫著:“彤彤乖,姐姐給你擦鼻涕。”
新源西裡小學的融合教育其實就緣自曉瑞和彤彤的這次交流。老師們發現,當告訴普通班的孩子這些特殊孩子只是一些生病的需要照顧的孩子時,普通孩子的愛心一下子被激發了。
當時朱振雲是特教班的班主任,劉老師是普通班的班主任,兩個班結成了手拉手班級。普通孩子有一個任務就是要給特殊班的孩子們講故事,“每個接到這個任務的孩子都覺得很光榮,他們會提前進行精心的准備,故事講得也特別好。”劉老師說。
每周,特殊班都會有兩個小朋友去普通班做客,普通班則會選擇最友善的兩個孩子負責接送。漸漸地,接送成了一件光榮的事情,大家都希望成為“最有愛心的孩子”。
孤獨症詩人迪金森曾經這樣寫道:沒人會記得這一朵薔薇/也許她從此就漂泊流離/要不是我從路邊撿起/送與了你。
“這個社會不是單面的,普通孩子不可能一輩子和普通群體打交道。”鄧猛教授說。
這種接納和包容在更小的孩子身上同樣可以看到。
在21世紀實驗幼兒園,普通孩子們早就習慣了東東隻吃同一種顏色的蔬菜,早就知道了東東不喜歡太吵的音樂,也知道東東需要別人照顧,孩子們會自覺地跟東東說話時放慢速度,當東東沒有回應時,他們也會再耐心地重復幾遍。
孩子往往是最具有包容和接受不同的潛能的,21世紀實驗幼兒園的劉園長說。
承認差異性的存在,教育生態就會發生變化
“普通的孩子學會與和自己不一樣的人交往的技能成為教育的必須。”鄧猛教授說。同時,對多樣性的關注,還會改變包括所有老師、家長在內的教育生態。
在新源西裡小學,這些特殊孩子帶來的最大的變化體現在老師身上:“老師們變了,開始拿孩子當孩子了。”朱振雲說。
特殊孩子的到來讓老師們直面差異的存在,養成了針對性教學的習慣。每個特殊孩子都會在學習周期開始的時候進行前測,由老師逐條具體分析薄弱所在﹔學習周期結束時進行后測,檢驗學習成果。每個孩子學習任務要求不同,有些學習障礙大的著重於生活自理能力的培養。
這種思維延續到了對待普通孩子的態度上。
原來經常能聽到老師們這樣評價孩子:這個孩子太淘氣,那個孩子總是坐不住。“但是現在我們的老師不再這麼看孩子了。”朱振雲說,老師們經常會找到特教老師說,自己班的一個孩子好像注意力有些問題,看到走路不協調的孩子馬上會聯想到肢體平衡問題。而且這些普通班的老師也會請特殊班的老師幫這些孩子設計一些方案,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
朱振雲記得一位老師鄭重地找到她,擔心一個學生的心理狀況,希望為這個學生做沙盤訓練。這其實是個普通班的老師,來學校不到一年。
“每個人都是有需要關注的特殊需求的。這需求落在正常閾值裡的,就是所謂的普通,這需求冒尖了的,就是特殊。”朱振雲說。
於是,資源教室的門不再隻針對特殊孩子了,特教老師也會對所有孩子的特殊需求提供幫助。
“如果針對所有學生的特殊需求,教學資源就不會浪費,學校執行起特殊教育也更有動力。”從事特教工作多年的宣武區特教中心潘鐳主任說。
當關注差異成為習慣,教育生態就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開始向教育的本質靠近。這種變化同時也在改變著家長。
“其實特殊孩子很敏感,中國式養育中的過度剝奪讓他們逆反。”朱振雲說。她曾在特殊教室裡備上了幾大箱的方便面,就因為在家裡家長不讓多吃。不出兩個月,孩子們迅速對這種自己痴迷過的垃圾食品失去了興趣。
家長們逐漸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教育理念也悄悄變化。一次家長會上,一位苛求的媽媽被其他家長“圍攻”,建議她對孩子放手。這位媽媽如今給朱振雲電話已能笑著說起這件往事,而她的兒子早已平和地升學了。
新源西裡走廊的一面牆上,孩子們花花綠綠的剪紙涂鴉中間,貼著一位老師寫作的小文,題為《我該如何愛》。在文中他說: 愛自己的焦慮,愛自己的不足……愛完整的自己。(樊未晨 王夢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