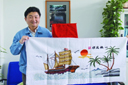北青报:哪方面?
朱清时:管理体制方面。学校在去行政化方面有很多变化,比如我们是唯一用理事会治理模式的公立大学;再者,南科大目前干部划分为两部分,学术干部如系主任、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等业务岗,都是没有干部级别的,由校长提名、在校务会上任命。只有管理干部即党政干部,仍然按照党委任命。这是南科大管理体制上的另一大改革。这5年,学校已经形成“教授治校”的文化与氛围。
北青报:可根据高等教育法,现在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校长与理事会的理念发生冲突了怎么办?
朱清时:他们都有各自分工,都是校领导。比如教务长主管教学,其他副校长就不管教学领域,也没有冲突。如果有人认为有行政级别的副校长比教务长要高一级,那就是他落后的观念。
北青报:回过头来看,该如何处理三者关系?
朱清时:这是南科大改革中最难的一件事。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刚才我所说,干部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把党委书记与校长的职权划分清楚,校长的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术干部,党委管党政干部,这就是我们做的尝试。
“国家的教育体制如果没有改进,光是一个学校去行政化是不可能彻底的”
北青报:关于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的成败,外界论断似乎比较悲观。
朱清时:去行政化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家的教育体制如果没有改进,光是一个学校去行政化是不可能彻底的。所以去行政化,我们说的第一就是干部管理,做好党委与校长职权的划分,学校形成教授治校的文化。
我们在学校的小范围内,能够做的都做了;如果还要做得更为彻底,那要等国家层面的改革带动。高校去行政化已经写到中央的改革决议里了。要有大的进展,只有等中央部署然后一步步来做。
北青报:所以说南科大也要等待?
朱清时:对,要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上级用行政化手段任命校长或党委书记,被任命者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只能对任命的人负责。所以还是要等国家把校长、书记的任命方式改革了以后才行。南科大改革其实最早、最关键的一项是校长的全球遴选,而非上级组织部门直接任命。遴选校长,是学校改革历程中最重要的起点,这点做到了,才有了后来的南科大。
北青报:一路走来,你对去行政化改革的最大感触?
朱清时:改革很难,涉及到很多规章制度甚至法律法规,但最难的是,需要一批参加实践的人。去行政化,最关键是人的观念。学校运作不完全按照谁的官儿大,就谁说了算,而要按照谁掌握办学规律,谁说了算。
我之所以被选为南科大校长,是因为我在中科大当校长时所做的事。当时,上级领导等各方面都要求学校扩招、建新园区。地方都想拉动经济,但我就想着要对中科大负责,扩招后,如果教师没有增加,中科大的“精”就会被稀释了。所以我坚决不做这些。
南科大遇到很多困难,最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缺少很多志同道合者愿意这样去做。如果各个岗位上都是这样对职务负责的人,去行政化就很容易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每个法官都坚持依法判案而不是按上级指示或打招呼,中国的司法大环境就会比目前好很多。
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如果每个校长都对自己的职务负责,过去一二十年教育走的那么多弯路,就可以避免了,对吧?
北青报:就像你在中科大当校长时曾说过的,“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
朱清时:其实很多人都明白这么做是对的,但是大家都喜欢合群的人。不合群的人是会被孤立的,别人会认为你要么太幼稚、要么太固执。
北青报:那您为何选择了改革,“跳车”后不怕被孤立?
朱清时:我是科学家、学者。当初45岁就做院士,后来做中科大校长时,很多老科学家都劝我说,你不搞科研而搞行政,太可惜了。所以我当中科大校长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我做校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要对职务负责。如果不能继续做校长,正好可以回到科研生涯中去。所以我没有担忧,随时准备卸任。
当中科大校长时最难也是我当南科大校长时想做得最好的,就是保住学校特点,而不完全按照谁官儿大,谁说了算。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