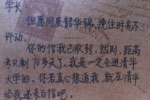胜诉可能也难实现预期效果
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关晓海看来,冒名顶替案的判决难点之一,在于对冒名行为的定性。
他曾分析一起案例。一个刘姓青年原在河南省某镇政府工作,后来离开单位前往南方打工。刘某家人认为岗位“轻易放弃甚为可惜”,便托关系安排刘某的弟弟刘二顶替其上班。三年后,刘二被人举报“冒名顶替参加工作”。
关晓海说,刘二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但法院审理认为诈骗罪并不成立。原因之一是,“行为人实施诈骗的主观意图是为了骗取财物,而刘二主观意图是顶替哥哥上班”。
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教研室副教授韩强认为,冒名顶替案的性质可分三个层次。在民法层面,冒名顶替无疑侵犯了被冒名人的姓名权;在刑法层面,如果利用冒名顶替从事诈骗活动,则可能上升为犯罪行为。
“再提高一个层次,比如‘齐玉苓案’,它可以认为是一个宪法问题,被侵犯了受教育权或者某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权利。这是一种宪法性权利。”韩强认为,对冒名顶替行为的定性,可能具有不同层次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
关晓海告诉中国青年报,以“齐玉苓案”为例,受教育权被侵犯的赔偿请求应该得到支持,但判决的难点在于如何确认赔偿数额。“根据民事填补损害赔偿原则,判多少才算填补损失呢?法官很难准确判定具体损失是多少。一方面,法官认可当事人权利确实受到侵犯,但另一方面,怎么救济成为了难题。”
他坦言,赔偿数额过多或过少,都可能让当事法官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韩强认同这种说法。他说,在冒名顶替案件中,损害赔偿往往属精神损害赔偿,核算金钱较为困难。按现阶段法院的做法,精神抚慰金数额较低,一般不超过10万元。
在齐玉苓获得的近10万元赔偿中,精神损害费为5万元,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各占7000元、4.1万余元。涉事学校、滕州教委对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其实,“赔偿损失”仅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之一。常见的救济方式,还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及恢复名誉等。
“但是,以恢复原状为例,有些事情可以恢复,有些事情无法恢复。”韩强举例,对于冒名考试的情形,被冒名者能否重考、录取资格能否重新分配等问题很难认定。尤其一些国家考试,更不太可能专门为某个当事人进行一次“恢复原状”。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法律承认它是侵权行为,但是提供的救济手段不充分。”韩强说,哪怕受害人获得胜诉判决,距离其希望的救济结果可能还相差甚远。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