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两月去盘溪买糖
带回来给孩子们吃
汤婆婆家的客厅茶几上,就放着一大罐陈皮糖,还有一罐时下流行的、名为“星球杯”的巧克力饼干和三筒麻饼,几乎占去了茶几的一半。茶几下方有层储物格,同样摆满了阿尔卑斯、雅士利、话梅糖等各种品牌的糖果铁盒———这些都是汤婆婆以前的“战利品”。
“这一桌糖果根本吃不了多久,最多每隔两个月我就会去盘溪市场买一次糖,每次都是5斤以上。”汤婆婆得意地说,因为经常去买糖,不少糖老板都以为她是开副食店的进货商,所以给她的卖价比普通零售价要低不少。
“我从小就爱吃糖,对糖有瘾。”汤婆婆说,自己小时候最盼望过节,因为过节就会有糖吃;“我在家里排行老三,还能得到哥哥姐姐的照顾,他们总会把父母原本平分给大家糖果,再匀两三颗给我。”说这话时,汤婆婆笑弯了眉梢,思绪似乎一下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妈妈的衣兜里永远都揣着糖,无论去哪里耍,她随时都摸得出糖吃,还经常剥好后喂我和老公。”儿媳妇李一菲告诉记者,受婆婆的影响,一家三口都爱上了吃糖:平均每个月的白糖用量至少要三四斤;每天早餐是“无甜不欢”,银耳汤要放糖,八宝粥要放糖,就连吃豆腐脑也要放糖。“亲友来我家吃饭,都说婆婆做的饭菜偏甜,但我们吃习惯了,觉得正合适。”
小区孩子想吃糖
一喊“糖婆婆”就有了
退休在家的汤婆婆,闲来无事喜欢一个人坐在窗前绣十字绣。她的家住在一楼,离地面堡坎约有两米高,客厅窗户外正对着的,就是绿化带和社区健身场,上面有乒乓台、健身器,成天都有一群孩子在玩耍。
“大的四五岁,喜欢结伴在这里打乒乓;小点才一两岁,常常在大人的陪伴下来这里练习走路。”汤婆婆说,她很喜欢孩子,没事时就一边坐在窗前绣十字绣,一边看着孩子们玩耍,还不时和带小孩的家长聊聊天,渐渐地和孩子们熟识了。
“这里的邻居基本上都是以前老江北城的,过去过来都是熟人。”汤婆婆说,每回她剥糖吃时,就顺便问这些孩子想不想吃糖,“刚开始时,大孩子还不好意思,个个都不吱声;反倒是年纪小的,都眼巴巴地把我望着。”汤婆婆说,她立马抓起一把糖跑下楼去,递到孩子们手中。
后来,常在健身场玩的孩子们都知道对面窗户汤婆婆家有糖吃。于是,有孩子们耍饿了,就会试着叫上一两声“汤婆婆”;结果,汤婆婆都会探出头来,然后抓起一把糖果下楼递给孩子……
久而久之,因为谐音,更因为糖的缘故,孩子们直接把汤婆婆叫做“糖婆婆”;而汤凤群也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因为腰痛不便频繁下楼,但她只要听到窗外有孩子喊、或看见孩子跟她打招呼,她就索性站在窗台边,如仙女散花一般直接将糖果从窗户里抛洒向绿化带和健身场———“糖婆婆”就此在小区里声名远扬。
旁边麻将馆的杨先生告诉记者,经常会有一群小朋友牵着手是来到窗户下,脆生生地喊“糖婆婆”,看上去乖得很,“每周至少都有三四次”———大家自然都会如愿以偿,捡起汤婆婆抛下的大把糖果,开心地满载而去。
邻居雷婆婆家2岁半的孙儿果果,便是汤婆婆窗下的常客。雷婆婆告诉记者,她和汤婆婆都是老邻居,关系挺好。“现在我们只要在楼下耍,果果自己都会屁颠屁颠地跑到汤婆婆窗下,去喊‘糖婆婆’要糖吃,我们喊都喊不住。”雷婆婆说,孙儿的行为,也在小区起了示范效应,小区里其他的孩子看到了也要跟着去,害得汤婆婆又要撒,“把别个汤婆婆的糖都吃光了,多不好得的!”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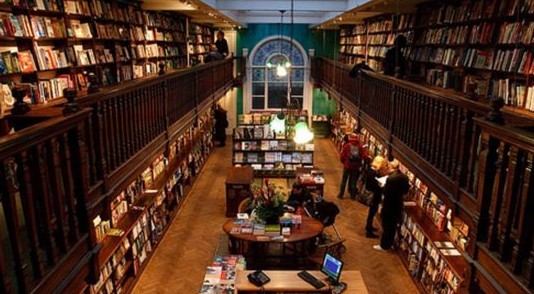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