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谷尋飛鳥,不覺夕陽斜——鄭作新院士與中國鳥類研究

圖片由作者提供。

1992年,鄭作新在閱讀資料。圖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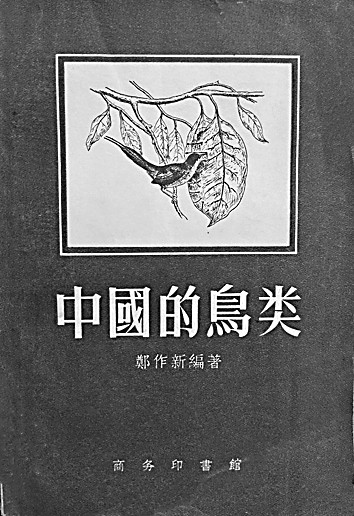
鄭作新編著《中國的鳥類》。 圖片由作者提供

1980年,鄭作新在標本室工作。圖片由作者提供

1978年,鄭作新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圖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學人小傳
鄭作新(1906—1998),福建福州長樂人。鳥類學、動物分類學研究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6年畢業於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獲學士學位,並考入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生物系,1930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任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等職。1950年任中國科學院標本整理委員會委員,1953年后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曾兼任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山東大學等校教授,中國動物學會理事長,中國鳥類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副會長,世界雉類協會會長。著有《中國鳥類名錄》《脊椎動物分類學》《中國鳥類區系綱要(英文版)》等。
1998年8月16日,第22屆國際鳥類學大會在南非德班開幕。一個多月前,大會名譽主席、中國科學家鄭作新不幸與世長辭。臨終前,睡夢中的他還在喃喃說著自己為大會准備的英文賀詞。開幕式上,大會主席宣讀了鄭作新的賀詞,全體與會者起立,為鄭作新和世界其他已逝鳥類學家默哀。
又是一個候鳥南飛的時節,我們又想起了這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鳥類學研究奠基人。
“不停地銜啊,叼啊,填呦填呦”
1906年11月,鄭作新出生在福建福州,5歲時母親病逝。在鹽務局任職的父親常年在外,奶奶擔起了家庭的重擔。奶奶常給鄭作新講故事,最打動他的是“精衛填海”。“不停地銜啊,叼啊,填呦填呦”,講到精衛鳥發誓要填平大海,從早到晚不停地叼來石子、樹枝時,奶奶總問:“你說精衛鳥決心大不大,毅力大不大?”而正是精衛鳥不屈不撓、鍥而不舍的精神激勵著鄭作新在求知和成長的道路上奮發進取。
鄭作新6歲上學,常常在油燈或蠟燭陪伴下苦讀到深夜。中學時的一天,他正在用功讀書,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暈倒在地。父親聞訊后,匆忙從外地趕回家。待鄭作新病情稍有好轉,父親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才這點年紀就病了一個星期,以后還要繼續念中學、上大學,為國效力,沒有健康的身體能行嗎?”從此,鄭作新開始頑強鍛煉身體,15歲,他在學校運動會上大顯身手,比賽結果張榜公布:“100米跑第一名鄭作新”“跳遠第一名鄭作新”“三級跳遠第一名鄭作新”。也就在這一年,他提前完成了中學課程——原本6年的學業,他隻花了4年時間。
當他報考福建協和大學時,卻被攔住了。“你給誰報名?”“我自己。”“你幾年級了?”“中學畢業。”“中學畢業?多大年齡?”報名處的老師看著這個稚嫩瘦小的孩子,滿腹狐疑。按規定,年滿16歲才能報考。報名處老師請來教務長,教務長甩了一句“你明年再來報考吧”。鄭作新所在中學的校長得知情況后,給協和大學寫了封十分誠懇的保薦信,懇請給這個孩子一個機會,讓他參加考試,考試不達標再退回來。協和大學答應了,但老師們紛紛“預言”:“能考50分就不錯了。”然而,他們預料錯了——閱卷老師看過鄭作新的試卷,脫口而出:“沒問題,准能錄取!”最轟動的是英語考試,無論筆譯還是口譯,鄭作新都答得又快又准,老師們激動不已。鄭作新終於被破格錄取。
在協和大學,鄭作新提前半年完成學業,隨即考入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生物學系。在密歇根大學,他邊打工邊刻苦學習,為醫院刷過瓶子,為系裡養過做癌症研究試驗用的白鼠。系裡的白鼠超過百籠,他每天早晚各巡檢白鼠一次,做好投喂、保潔和記錄,根本沒有休息日。由於學業優秀,工作出色,他被聘為助教。
解剖一隻青蛙,再解剖一隻青蛙……誰也說不清鄭作新那時究竟解剖過多少青蛙。他的畢業論文《林蛙生殖細胞發育史》在德國科學刊物《細胞研究和超微形態學報》發表。20世紀20年代,德國處於科技最前沿,德國科技雜志很少發表外國論文,卻刊發了一位中國青年學者的英文論文。有德國科技界人士稱,該論文提出了一些新觀點,行文簡潔流暢,是細胞學研究方面的一篇杰作。23歲時,鄭作新獲得博士學位,並被授予“金鑰匙獎”。
中國鳥類豈能隻由外國人研究
在密歇根大學,鄭作新除了讀書、做實驗,就愛鑽博物館。一次,他在學校博物館欣賞著來自世界各地琳琅滿目的動植物標本,突然,一隻美麗大鳥映入眼帘——頸部圍裹著扇狀金棕色羽毛,肚皮通紅,長長的尾巴上桂黃和褐色波狀斑相間呈現。這不是棲息於中國腹地的“金雞”——紅腹錦雞嗎?它也被譽為寶雞,隻產於中國,飛翔於秦嶺渭水之間,相傳陝西寶雞的地名就是由此而來。明明是中國的“寶雞”“金雞”,卻由瑞典生物學家林奈於1758年發現,並依國際慣例以拉丁文命名。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先秦典籍《詩經》就以鳥開篇,然而,早年間科學意義上的中國鳥類研究專著卻全部由外國人撰寫——英國人斯溫侯的《中國鳥類名錄》(1883年)記載中國鳥類454種,1875年法國人戴維斯的專著擴充為807種,美國人祁天錫等的《中國鳥類目錄試編》記載更多——1931年修訂后擴展為1093種,575個亞種。這深深刺激著血氣方剛的鄭作新:中國鳥類豈能隻由外國人研究著述?他立志撰寫中國人自己的鳥類研究專著。這意味著,他要放棄已經小有所成的胚胎學研究,選擇鳥類學作為自己的專業。
1930回國后,鄭作新回到母校福建協和大學任教授。鳥類研究浩繁艱巨,資料經費奇缺,困難重重。鄭作新在繁重教學工作和勤奮閱讀之余,開始了艱苦的野外考察和資料採集工作。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進逼福州,協和大學被迫遷至武夷山腳下的古城邵武。武夷山地處“東洋界”和“古北界”兩大動物地理界區交匯邊緣,在不同高度有著不同氣候條件和生態環境,是脊椎動物和昆虫新種模式標本產地,有我國動物標本“鑰匙”之稱。每當晨曦微露,伴著清脆鳥鳴,崎嶇陡峭的山上就會出現鄭作新及其幾名學生的身影。他們每次觀察兩小時,每周繞山而行一兩次,對鳥的種類、遷徙、繁殖、數量消長等進行考察研究,一干就是三年。
其間,鄭作新在閱讀國外資料時得知,武夷山深處還有一個“世外桃源”——小鎮挂墩,堪稱鳥的王國,國外許多鳥類標本就是從那裡採集的。其具體位置,連當地時任縣長都不知道。1939年暑假,他帶領5名師生從邵武出發,一路打聽,越層巒,穿密林,渡山澗,涉小溪,戰風雨,跌倒了爬起,再跌倒再爬起,雙腳腫痛,兩臂晒紅,走了七八天終於抵達挂墩,搜集到大量鮮活資料。1941年,鄭作新的《三年來邵武野外鳥類觀察報告》發表,這是國內第一篇鳥類及其生態的實地考察報告,深受科技界重視。1944年,他赴美進行學術交流。在福建一些地區被日軍封鎖狀態下,鄭作新要繞道而行,當他所搭乘的飛機飛經湖南敵佔區時,遭到日軍高炮攻擊,幸而沒被擊中。在美國,鄭作新受聘為客座教授,他抓住機會,深入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芝加哥自然博物館、哈佛大學等查看鳥類標本、搜集資料。母校密歇根大學邀請他回校做博士后,他拒絕了,而是帶著幾大箱筆記和資料返回祖國。
回到協和大學后,他爭分奪秒,悉心整理研究和比對資料。他發現,祁天錫等人的《中國鳥類目錄試編》所記載的一些鳥類是同物異名或材料不實,應刪除和修正的竟有200個左右,學名該更正的為數更多。1947年,鄭作新的《中國鳥類名錄》面世,所列中國鳥類1087種,912個亞種,總計1999種,不僅在種類上超過以往外國研究中國鳥類的專著,而且對外國專著中的鳥類學名以及差錯做了大量更正,為新中國鳥類全面考察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探明中國鳥類資源
新中國的誕生結束了頻仍戰亂,鄭作新得以更為深入地研究祖國鳥類。他深知《中國鳥類名錄》雖有成就,但受當時條件所限,一定還有許多鳥類未列其中,尚待發現和研究。為此,他一直渴望對全國鳥類資源進行廣泛考察。
鄭作新被調到北京,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后任該所研究員。中科院接受了他和其他專家的建議,動員全社會力量開展有史以來首次全國鳥類普查。他親率科考隊,走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風餐露宿,夜以繼日,以林為家,與鳥為伴。1951年在河北昌黎林區,連續幾十個日夜,鄭作新和同伴輪流守在鳥巢附近的草叢中,一刻不停地觀察鳥類活動。為了避免驚動鳥類,影響觀察效果,他們常常一個姿勢保持幾個小時,腿麻了也不挪動一下,螞蟻爬到臉上、夜露浸濕衣服依然穩如泰山。
在四川採集標本時,山高路險,鄭作新及其團隊冒著隨時可能墜落深淵的危險,攀著岩石和大樹行走在陡峭山谷間。一次,他們涉水渡河,正趕上山民打開閘門,利用湍急的河水向下游放流砍伐好的樹木。隻聽一個當地小孩用方言高喊“莫忙走”(意為“別著急走”),考察隊員誤聽為“莫慢走”,從而加快腳步,兩位年輕隊員剛踏入水中,幾根粗大的樹木順流而下,飛速扑來,走在前面的隊員瞬間被樹木裹挾進急流,不幸殉職,鄭作新與他僅相隔幾米。
雲南大圍山考察,在隻能行走一匹馬的狹窄險峻山路上,由於晝夜兼程,人困馬乏,考察隊一匹馱滿禽鳥標本的馬落入千米深淵,鄭作新也因體力不支從馬背摔下,跌傷肋骨。然而,就是這次大圍山考察,鄭作新及團隊發現了畫眉類新亞種——斑胸噪鹛大圍山亞種。
在黃山考察時,鄭作新已50多歲。下山時坡陡路險,他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往下蹭,一條咔嘰布褲子愣是磨得滿眼孔洞,而下山后他還要去省城參加會議,來不及更換,他干脆就穿著一條千瘡百孔的褲子出席會議。
1960年,鄭作新一行赴峨眉山考察,在山坡上,他們遇到一位老獵人。老人熱情邀請他們到自己的茅屋休息。茅屋牆壁上懸挂著老獵人剛捕獲的幾隻鳥。鄭作新立即被其中一隻吸引,隻見它紅紅的冠子后面披著幾縷散發寶石藍般光澤的藍色羽毛,還有著長長的白色尾羽。是白鷴!從李白“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鷴。白鷴如百錦,白雪恥容顏”的詩句中,即可認識白鷴的珍貴。當天,鄭作新在獵人祖孫的帶領,在野外發現了白鷴。
根據系統分類學理論,一種動物隻有一個發源地,以此為中心逐漸向各方擴散。而這個理論下又有兩種見解,第一是一個種的劣勢(低等)亞種留在發源地,優勢(高等)向外擴散﹔第二是一個種的優勢(高等)佔據發源地,劣勢(低等)被排擠到邊遠地區生存,這也是鄭作新的觀點。白鷴有10多個亞種,生活在越南、柬埔寨等熱帶或亞熱帶地區,我國海南、雲南和兩廣等地也有,在其以北數百公裡的峨眉山,國內學者還沒有發現過。是有人放生白鷴於峨眉山,還是它本就生存於此?鄭作新將峨眉山的白鷴與南方白鷴反復對比,仔細研究,終於發現:南方雄性白鷴白色尾羽中夾雜的是黑色細紋﹔峨眉雄性白鷴尾羽主色也是白的,但左右兩邊的外側尾羽卻是黑色的,而背部、翅膀和肩部的黑色細紋和南方雄性白鷴在粗細、長短和間距上也不相同,因為差異不明顯,很容易被忽略。鄭作新研究認為,峨眉白鷴是土生土長的種群,是一個新亞種,並將其命名為“峨眉白鷴”,這一成果寫成論文於1964年發表在《動物學報》后,國際學術界也確認這是白鷴的新亞種,是白鷴研究新發現。西方國家鳥類科研已有二三百年,再發現新種和新亞種可能性微乎其微。新中國鳥類研究人員發現的新亞種有20多個,其中16個是鄭作新引領發現的,他通過歷次野外考察,採集了成千上萬件各種鳥類標本,獲取了祖國大量鳥類生態及分布資料。如今,中科院動物研究所收藏有鳥類標本60000余件,是舊中國北平動物研究所和靜生生物調查所所存鳥類標本之和的20倍,成為我國最大的鳥類標本庫。
每次從野外考察回來,鄭作新都會對採集的標本進行整理鑒定,結合有關專著和論文,標出拉丁文學名,核查是否同物異名,繼而撰寫文章,發表成果。晚年身患心臟病、白內障等疾病的他,工作兩小時就要躺下吸氧,依然靠放大鏡工作、寫作。他撰寫了《中國鳥類分布名錄》《中國經濟鳥類志》《西藏鳥類志》《中國鳥類種和亞種分類大全》等專著30余冊,研究論文140余篇,科普文章260多篇,總計1000余萬字。其中,1987年出版的以英文撰寫的《中國鳥類區系綱要》約120萬字,列入我國截至1982年年底已知全部鳥類,共計1186種,935個亞種。書中把國內鳥區分為留鳥、候鳥、繁殖鳥、旅鳥等,為國家動物保護法提供了具體資料。該書於1988年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和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在國際學術界也獲廣泛好評。1988年,美國國家野生動物協會授予鄭作新國際動物資源保護特殊成就獎。鄭作新捐出中科院、國家科委等部門給予《中國鳥類區系綱要》的獎金,設立了“鄭作新鳥類科學青年獎基金”,以獎勵對我國鳥類研究貢獻突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1994年出版的《中國鳥種類和亞種分類名錄大全》共列截至1992年我國已知鳥類1244種和944個亞種,這一數字約佔當時全世界已知鳥類9200種的13.5%,相當於歐洲和澳洲鳥類種類的總和。
伴隨鳥類資源的探明,我國鳥類資源的地理界也被鄭作新糾正。在鳥類分布上,全世界分為6個地理界,即古北界、新北界、東洋界、熱帶界、新熱帶界和澳洲界。中國擁有古北界和東洋界兩個動物界,全世界也隻有中國和墨西哥擁有兩個動物界,這也是中國鳥類種類多於美俄等國的主要原因。然而,對這兩界的劃分定界,學界過去採用英國人華萊士1876年的論斷——以南嶺為界。鄭作新根據對中國鳥類資源的考察和研究,結合土壤、植被、氣候等資料,指出應以秦嶺為界,繼而在兩界中又劃分出4個亞界、7個一級區和19個二級區,得到學術界贊同和支持。
為中國鳥類溯源正名
在殫精竭慮探明祖國鳥類資源的同時,鄭作新也發現,一些既有的研究結論並不正確。
達爾文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中寫道:“雞的家養是在《摩奴法典》完成的時候,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雞是西方的動物,是公元前1400年的一個王朝時代引到東方中國的。”達爾文認定,家雞源於印度,然后經由中國傳到歐亞各國。一度,歐美、日本以及中國的家禽學著作都寫明中國的家雞引進於印度。鄭作新思考,中國歷史悠久,古代中國生產力並不低,為什麼中國的原雞不會被馴化成家雞?為什麼要從印度引進?他反復閱讀達爾文的著述,發現達爾文的根據是1596年出版的所謂“中國百科全書”。鄭作新查閱大量資料,確認那本“百科全書”原來是1609年(明萬歷三十七年)印刷的《三才圖會》,書中一段話是:“雞有蜀、魯、荊、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尤其大者,舊說日中有雞。雞,西方之物,大明生於東,故雞入之。”中國古代把印度稱作西天,如唐玄奘西天取經。鄭作新經研究認為《三才圖會》中的“西方”指的不是印度,而是指中國西部。科學結論需要科學証據。1957年,他和助手到雲南考察鳥類資源,經多日艱辛尋找,在當地發現了幾隻形態酷似家雞的茶花雞,它們正混入家雞群與之嬉戲。經過一系列科學考証,鄭作新得出結論,茶花雞是中國的原雞。此后,各地史前遺址考古發掘特別是雞形陶器的發現也証明,中國對雞的馴化遠早於印度。而甲骨文對雞的記載,也不晚於《摩奴法典》。20世紀90年代,學者利用現代技術手段對原雞與家雞間的親緣關系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我國4個家雞品種在系統中歸於一個類群,而國外的不同原雞聚類為另外的類群,中國地方雞種有獨立的血緣來源。中國家雞起源於中國,鄭作新的研究成果糾正了達爾文的錯誤結論,獲得國際學術界認同。
20世紀50年代中期,全國掀起“除四害”高潮,麻雀同老鼠、蒼蠅和蚊子一起被列入“四害”,一時間全民動員捕殺麻雀。其間,中國動物學會召開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討論了麻雀問題,爭論激烈。會上,有人引証了19世紀法國政府曾下令懸賞滅除麻雀的實例——每消滅一隻麻雀獲賞6生丁(1法郎等於100生丁),麻雀被大量捕殺,但因自然生態遭破壞,導致果樹虫災嚴重,水果產量銳減。作為時任學會秘書長,鄭作新提出了個人觀點。他認為,麻雀消滅不了,因為其分布是世界性的。麻雀在飼雛期間以昆虫為食,能夠除掉害虫而有益於人類。我們對它的科學研究還不充分,為麻雀定性需要科學証據,要“防除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本身。
鄭作新不忙於作結論,會后,他和同事深入北京郊區農村和河北省昌黎果產區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調查研究,採用解剖嗉囊的方法研究了848隻麻雀標本,同時又進行了籠養試驗,推算麻雀對某種食物的食量。結果表明,冬季麻雀以草籽為食,春季下蛋孵卵,大量捕食昆虫及虫卵,幼鳥食物中,虫子佔95%,七八月間成鳥帶領幼雀離巢飛往農田,主要啄食剩谷和草籽。在農作物區,春夏之交麻雀大量捕食害虫,對人有益﹔秋收期間糟蹋糧食,對人有害﹔而在城市和林區,麻雀對人無害。1957年,鄭作新和助手們寫成《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報告》在《動物學報》上發表,並在《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文章,談麻雀的益與害。科學家的意見受到重視,1959年的農業發展綱要進行了修改——“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后來,“四害”中的麻雀被臭虫取代。
1980年1月,以丹頂鶴研究和保護為主要議題的國際鶴類學術會議在日本札幌召開,鄭作新作為團長率中國學者代表團參會。
丹頂鶴主要分布在我國、蘇聯遠東地區、蒙古國、朝鮮半島和日本北海道。對丹頂鶴的叫法國際學術界並不統一,多數用英文Japanese crane,會議主辦國日本就是使用這種叫法。但是,這種叫法不僅容易使人誤解為丹頂鶴僅僅指“日本的鶴”,而且還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即丹頂鶴是典型的候鳥,而日本北海道的丹頂鶴從1952年起每年冬季在釧路濕原設點吃食,已失去南北遷徙的候鳥特性,成為留鳥,當時已知其種群有200多隻。亞洲大陸丹頂鶴情況不同,分布區廣大,涵蓋黑龍江流域至長江中下游和朝鮮半島等,種群數量遠遠超過北海道,並都保存著季節遷徙的典型候鳥習性。鄭作新在會上建議:“大家知道,丹頂鶴是亞洲特有鳥類,分布很廣。為名稱統一,便於國際交流,關於丹頂鶴的英文名稱我們統一叫Red-crowned Crane,好不好?”會場沉寂了片刻,繼而主持人帶頭鼓掌,會場一片掌聲,大會通過以丹頂鶴的中文直譯命名其英文名稱。此后,國際鶴類文獻的英文名稱通常使用鄭作新建議的英文命名。
鄭作新一面投身學術事業、培養學術人才,一面撰寫科普作品、關注野生動物保護,倡導設立丹頂鶴自然保護區和“愛鳥周”,提出愛鳥工作要落實“三保”(保護、保育、保全)。他的心中有對科學的向往,也有對鳥語花香、生態多樣、美麗中國的憧憬。有人說“鄭老是座山”,誠哉斯言。
(作者:馬躍,系光明日報主任編輯)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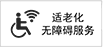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