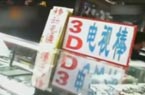放眼古今中外,抒发思乡之情的诗文千千万。笔者个人感受,唯有用古老的文言,才能唱出如此回肠荡气、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笔者同样怀疑:时下国人语言之粗鄙低俗,整体文化教养之令人失望,是否也与文言传统的断裂有某种关系?
2009年,由于受陈水扁台独政策的影响,台湾修订了《高中国文课程标准》,将文言文的比例由此前的65%缩减至55%,台湾文学家、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撰文对此提出严厉批评——
新文学之兴起,迄今不满百年,百分比却要超过数千年的古典文学,实在轻重倒置。古典文学的杰作历经千古的汰芜存菁,已成文章之典范,足以见证中文之美可以达到怎样的至高境界。让莘莘学子真正体会到如此的境界,认识什么才是精练、什么才是深沉,在比较之下看出,今天流行于各种媒体的文句,出于公众人物之口的谈吐,有多雅,有多俗,多简洁或多繁赘。文章通不通,只要看清顺的作品便可,但是美不美,却须以千古的典范为准则。
中华民族所承受文化的内容,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以文言为载体的启蒙,不仅是“识文断字”,而是“启”人文之“蒙”,包括百科常识教育、历史教育和经典教育,正好对应着现代课程理论的三个范畴:知识—价值—思维方式,背后则隐含着以经学、史学、文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知识结构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个体,启蒙教育的意义自不必论。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启蒙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并有其鲜明的特色。据史书记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众多小学识字教材。并且,其教材内容、编写体例、语言方式等均已形成基本模式,以后各代及至晚清,前后长达两千年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这种惊人的“超稳定性”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征。
在语言形式上,历代识字教材多为韵文。如公元前40年成书的《急就篇》,是我国现存比较完整的最早的小学识字教材兼常识教材,西汉时史游编纂,全书共2114字,34章。此书主要把当时日常所用单字按姓氏、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分类汇编,成为三言、四言、七言韵语,既便于记诵,又切合实用,并尽量避免重复字,同时尽量使每句都表达一定的意义,以使儿童在识字过程中多获得一些自然及社会常识。
后世研究者这样评价《急就篇》:“我们在这里可以见到与当时人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目,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于人体生理和疾病、医药的知识。这里列举了种种农具和手工工具,各种谷物和菜蔬,各种质地和形式的日用品,各种色彩和花纹的丝织物,表现了这个铁器时代的人们与自然作斗争的规模。”
《急就篇》以这样的文句来结束:“……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今天我们诵读这些节奏铿锵、一气贯成的四言韵文,仍会感受到一种泱泱大国的雍容气度,以及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自信自豪。
比较时下碎片化的小学语文教材,《急就篇》分明建构了一个小百科辞典式的知识谱系,一个关乎天地宇宙人间的大系统。而与此同时,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汉代社会图景。对于混沌初开的儿童来说,这种“启蒙”的价值已不仅仅是“识文断字”,而是“启”人文之“蒙”。
有意思的是,2010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浙江温州一个名叫李山的偏僻山村里,发现一册名为《簿记适用》的乡村识字教材,其编写体例几乎与《急就篇》一模一样,同样是小百科辞典的范式,同样是四言、七言韵文,只是内容与当地的人文地理习俗密切相关,故又称之为《李山书》。编写时间为1918年,距《急就篇》近两千年。编写者为当地一位小学校长。
可以说,《急就篇》奠定了中国启蒙教育阶段识字教材的基本范式。其后又过了500多年,即公元535~545年,梁武帝大同年间,周兴嗣所撰作的、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首句的《千字文》问世。《千字文》继承了《急就篇》的编写范例及韵文形式,并成为后世1400多年来被使用最广泛的识字教材,且一字不改。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同样的范例。对此,笔者不禁怀疑“与时俱进”这句话的普适性——至少在母语教育方面。
从内容上,中国启蒙教育也很重视历史教育和经典教育。前者现存可查的为唐朝时盛行的《蒙求》。《蒙求》全文596条,计2384字,以历史典故为内容。四字一句,两句一联。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桓谭非谶,王商止讹。孙康映雪,车胤聚萤。西门投巫,何谦焚祠。”其中很多典故成为后世蒙学读物《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取材来源。《龙文鞭影》正文8200字,录取了2000多个故事,内容包括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著名的人物故事、历史故事、神话、寓言等,相当于一部生动有趣的简明中国通史。
经典教育则可上溯到汉代。据载,当时学童过了识字关后,接着便进入学习经书阶段,所读内容为《诗》、《书》、《礼》、《易》、《春秋》,加上《论语》和《孝经》。主要方式为“诵读”,即只要求是对经书“粗知文义”或“略通大义”,不求深解。从唐宋以后,《论语》和《孝经》作为最常用的蒙学教材,一直沿用到1949年后私塾被取消。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启蒙教育包括的三大部分内容:百科常识教育、历史教育和经典教育,正好对应着现代课程理论的三个范畴:知识—价值—思维方式,背后则隐含着以经学、史学、文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并由此奠定传统中国人的宇宙观、历史观和伦理观的基础。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指出:“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
我们也许可以断言:正是这样一种以人文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启蒙教育,维系了中华文化于不坠。而承载这种教育内容的语言形式便是文言文。在这个意义上,文言是中华文化之“源”,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推广的白话只是其“流”。笔者不禁怀疑:当下中国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能否无视这样一个长达两千年的历史经验之存在,而仅仅依据最近百年乃至60年的“流”,来制定关乎民族未来的教育策略?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