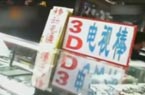无独有偶。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从小在上海长大,每到寒暑假,身为律师的父亲专门为他延请一位家庭教师,指导他读《论语》、《孟子》,还有《古文观止》等,且都要背诵。值得注意的是,杨、高二人的父亲均受过严格的西方教育。
除这两位科学家外,还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胡适、陶行知、陈寅恪、郭沫若、钱穆、竺桢、邹韬奋、朱自清、朱光潜、郁达夫、徐志摩、茅以升、梁漱溟、李四光、蒋梦麟、顾颉刚、傅斯年、丰子恺、鲁迅……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单如果一直列下去,几乎囊括了近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界的杰出人才。而他们早年,均接受过传统的“之乎者也”的教育。
而另一面,即使在新式学校里,国文教师也并不全用语体文教科书教学。笔者采访过多位在1930~1940年代念小学或中学的学者。老先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笔者,当时上小学时学的还是语体文,但到了初中、高中则几乎全是文言文。邓云乡先生在其著作《文化古城旧事》中提到当时高中生须会写文白两种文体的文章,“……因为考大学时,像北平北大、清华这类学校,大都出白话文题目,而南方上海交大、南京中央大学等,则都出文言文题目,高中毕业生必须学会写两种文体的文章……”至于高中国文教材,不少学校直接采用古文选本,如《古文观止》《古文释义》等。
即便是教会中学也不例外。北京汇文中学第十任校长高凤山先生曾留学美国,先后获美国西北大学文学硕士、波士顿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1936届校友何纯渤先生这样回忆道:“我们老校长(高凤山先生)提倡文言和白话并重。我进学校半年就体会到这个好处。”他还记得老校长说过的一句话:“新的东西都是从旧有的东西传下来的。没有旧的就没有新的!”
不仅是家庭和学校如此,一些社会出版机构也顺应这种趋向。作为最早编印中小学新式教科书重镇之一的中华书局,在编印小学语体文教科书的同时,还出版了一系列普及型的文言读物,如《古文比》(全四册)、《史记论文》(全八册)、《五朝文简编》(全廿八册)、《文学精华》(全廿二种)、《古今文综》(全四十册),等等。其中特别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一套供高等小学校用的《评注古文读本》(全六册),每册30篇。此书首印于1916年12月,至1933年3月止,17年间印行33版次。以当时全国识字人口来看,这个数字已相当惊人。
另外,中华书局还分别在1923年和1925年编过一套新中华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三册)和《高级古文读本》(三册),两者与同时期编写的《初级国语读本》(三册)、《高级国语读本》(三册)并行不悖,形成文、白分编两套教科书,在当时颇有影响。
颇有意味的是,1948年,白话文的倡导者叶圣陶、朱自清和吕叔湘三人合编了一套《开明文言读本》,为当年开明书店汇集一些名家编印的系列国文教材中的一种,原计划出6册,实际只出了三册。1978年,叶圣陶、吕叔湘先生删去《开明文言读本》中若干篇课文,将原来的三册合并成一册,即为《文言读本》,由三联书店出版。编者在《编辑例言》中说:“我们把纯文艺作品的百分比减低,大部分选文都是广义的实用文。”书中一共选了32篇文章,从体裁上有小品、佛经、笔记、序跋、小说、古风、近体律绝、家训、政论,等等。作者则上至先秦,下至鲁迅、蔡元培,各代都有。编者还特意编排了一些白文,供学生断句和标点。
由此可见,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尽管移植于西方的现代新教育已从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上全面改写传统中国教育,小学语体文教科书代替了“三百千千”,“狗,大狗,小狗(1922年商务印书馆《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代替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民间,文言文与语体文呈现出二水分流、双峰并立的景象,两者一旧一新,相济相生,使得三千年的文言血脉得以延续,文化的薪火不至于中断。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