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種未來的追夢人——追記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學家鐘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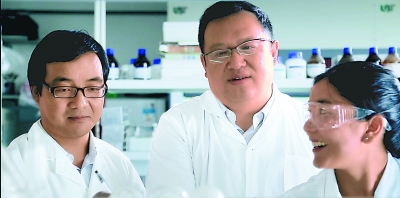
鐘揚(中)和學生在一起。 (復旦大學供圖)
他有很多頭銜和成就——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西藏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發表論文200余篇,獲國家發明二等獎一次,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三次……但他更願意稱自己是“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學家,一名來自上海的援藏教師”。他說,人這一輩子,不在乎發了多少論文,拿了多少獎項,留下來的是故事。
他有很多傳奇——15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畢業后從無線電專業轉行植物學和生物信息學,短短幾年就站上這一領域的學術前沿﹔33歲時已是一名副局級干部,前途一片大好,卻毅然放棄所有職級待遇,來到復旦大學做一名普通教授﹔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30余年,學術援藏16年,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萬公裡,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幫助和推動了西藏大學的植物學專業從“三個沒有”:沒有教授,教師沒有博士學位,沒有申請過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到創造一個又一個“第一”,不僅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空白,更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他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參與SARS病毒和血吸虫基因組的進化研究,獲得重大突破﹔科普類暢銷書《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的中文版譯者﹔2010年上海世博會英國館種子殿堂裡40%種子的提供者﹔義務參與上海科技館科普工作17年,撰寫大量中英文圖文版,是深受青少年歡迎的明星專家和科學隊長。
他叫鐘揚,一位擁抱時代的先行者,一位播種未來的追夢人,他是先鋒者,更是奉獻者。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追逐夢想,都在奉獻祖國,他是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學家。
2017年9月25日清晨,在為民族地區干部授課的出差途中遭遇車禍,鐘揚53歲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消息傳開,網上網下,人們自發地追思他,懷念他。
他說,最好的植物學研究一定不是在辦公室裡做出來的,祖國那些生物資源豐富的地方才是生物學家最應該去的地方。所以,他選擇了西藏,因為那裡是國家生態安全戰略重地。從2001年起,鐘揚10年自主進藏開展科研,此后更連續成為中組部第六、七、八三批援藏干部。
16年間,他的足跡遍布西藏最偏遠、最艱苦、最荒蕪的地區,經歷過無數生死一瞬。他一直對學生說,“隻要國家需要、人類需要,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去做”“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他深知,種質資源事關國家生態安全,事關整個人類未來。他致力於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他把論文書寫在祖國的山川大地,他用生命在天地之間寫就壯闊的時代故事。
2015年,鐘揚突發腦溢血,死裡逃生蘇醒后,第一時間口述記錄下一封給黨組織的信:
“這十多年來,既有跋山涉水、冒著生命危險的艱辛,也有人才育成、一舉實現零的突破的歡欣﹔既有組織上給予的責任和榮譽為伴,也有竇性心律過緩和高血壓等疾病相隨。就我個人而言,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在同事的記憶裡,他是與時間賽跑的人。他的衣袋裝著很多小紙片,上面密密麻麻寫滿待辦事項,每做完一項就用筆劃掉。每次出差都選擇最早班飛機,隻為到達后就能立即開始工作﹔他常在辦公室工作到半夜,鬧鐘固定設在凌晨3點,不是用來叫他起床,而是提醒他到點睡覺﹔突發腦溢血后,隻住了十幾天醫院就重新投入工作,而當時的他甚至連午餐盒都無法打開﹔他的隨身聽裡是請學生錄的藏語聽力教材,他說:“沒人規定援藏干部要學藏語,但是用藏語,是表達尊重的最好方式。”
“在我的課題組裡,學生才是上帝。”這不是鐘揚的一句玩笑話,在他的實驗室裡,每個學生做的都是最適合自身的研究。在他眼裡,每個學生都是一顆珍貴的種子。就像收集種子一樣,他用心培養,因材施教,期待他們長成參天大樹。鐘揚特別喜歡招收少數民族學生,他認為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人才尤其難,但培養好了,這些學生回到家鄉,就能成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軍。十幾年間,他培養的學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雲南等西部省份。他說,“我有一個夢想,為祖國每一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
忙碌的科研教學之余,鐘揚還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大眾科普教育事業。在他看來,最應該做科普的就是一線科學家。他說,科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事業,而科學家的特質就是從中提取歡樂,然后把科學和歡樂一起帶給大家。
歷經多個領導崗位,鐘揚永遠嚴格自律、簡朴廉潔。一條29元的牛仔褲陪他跋山涉水,3件短袖襯衫就可以過一個夏天。他從不對職務待遇、收入條件提任何要求,他心裡想的隻有做事,做對國家有用的事。
告別會上,鐘揚80多歲的父親對治喪小組提出了家屬唯一的要求:“隻希望在悼詞裡寫上,‘鐘揚是一名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記者 顏維琦)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