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山裡中學演繹的“逆襲”故事
鄭漢超聽說,進了毛中的學生,如果想成為成功故事的主角之一,就必須接受和適應這裡的規則。
這套規則,是“毛中制造”的核心肌理。毛中分管教學的副校長李振華,將其概括為“全方位立體式無縫管理方式”。畢竟,這座“工廠”的人數規模很龐大。在補習中心上課的超過8000個學生,下課鈴響后同時從教學樓往外走,直到整座樓空無一人,要花去將近15分鐘。
這裡有嚴苛的時間作息制度。一天24小時會被一張作息表嚴絲合縫地分解掉。通常,早上6點10分進班早讀,直到晚上10點50分下晚自習,休息時間隻包括:午飯、晚飯各半小時,午休1小時——午休本是兩小時,但學生被要求到教室睡覺,順便再勻出1小時自習。
有的班主任甚至還要求“統一上廁所”,“以免進進出出影響別人休息”。
毛中的老師們認為,應對標准化的考試,需要大量和重復的訓練,因而在這裡經受“鍛造”的學生,“1年要完成過去3年才可能做完的習題和考試卷”。
在這座“高考工廠”裡,競爭的氛圍被制造得很濃烈。高三幾乎每周都要考試,成績表張貼在教室門外,排名靠后的名字會被紅色的橫杠標注。
為了給“毛中制造”提供優質而又勤勉的人力資源,學校在招聘老師時明碼標價“年收入6∼10萬元”。大部分毛中老師生活水平都不錯,可以在六安或者合肥買房,還開上了私家車。
但是,對於老師們來說,這座“工廠”的生存法則非常殘酷。學校選聘班主任,每學期根據考試成績,實行“末位淘汰制”,而班主任可以炒掉任課教師。
近年來,全國各地的高中校長、教師和家長來毛中取經問道的不少。幾年前,深圳市福田區教育局也曾到這個皖西山坳裡來參觀交流。
在校領導看來,毛中的門道,“一點兒都不神秘”。它在校園裡幾乎隨處可見,被賦予各種形式向人們展現——可能是學校花壇裡寫著“肯吃苦才能代代成才,守規矩方可日日進步”的宣傳牌,也可能是教室牆壁上直截了當的“為了大學,拼命吧”的勵志標語,或者是老師們愛說的那句口頭禪“兩橫一豎,干!”
這一切都成就著毛中的高考“神話”。曾經很長一段時間裡,毛中只是一所不為人知的山區學校,而且它隨時面臨著和其他鄉鎮中學類似的命運——在教育資源不平衡的背景下,逐漸衰落。
如今的毛中,演繹著一個“逆襲”的故事。這個地處大別山余脈的中學,正在修建田徑館和游泳館,還在操場上立起一塊巨大的LED電子屏幕。毛中的老師自豪地說:“這是華東地區最大的一塊電子屏幕。”
有人認為毛中是“高考聖地”,也有人說它是“地獄”,隱喻著中國高考的畸形和異化。在毛中經受過鍛造的人,在網絡上宣泄著對母校的復雜情緒。有的人對它很痛恨,也有人說:“對毛中充滿感激。”
信奉毛中“神話”的家長和學生,還是在使勁兒地往那扇門裡擠。很多人認為,隻要一腳踏進毛中大門,就意味另一隻腳踏進了大學。
8月的最后一天,一位六安當地人幫著一對來自廬江縣的農村夫妻,往復讀班的教室裡硬塞進一張黃色課桌。講起這事時,他咬著牙,雙手在半空中環抱,比劃著為挪動那張課桌費勁的樣子。
這位不付重托的朋友,在那對夫妻面前,拍著胸脯說:“放心吧,進了毛中,你們女兒來年高考一定能漲分。”
安徽當地人認為,托關系將親友的孩子送進毛中,“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現實是,也有好不容易擠進毛中的學生,在這裡呆了一兩天,就哭喊要逃離。
復讀班開課后第二天,一個戴著眼鏡的小個子女生站在教室門外抽泣。她拖著哭腔向一位中年婦女哀求道:“媽,我真的受不了。我一看到,那麼多書,太恐怖了。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不讀了,不讀了。”
穿著套裙、腳踩高跟鞋的母親,臉漲得通紅,恨恨地說:“你不讀?你為什麼不讀?這麼多人不是都在讀嗎?你知不知道,為了能讓你上這個學,我已經煩透了!”
她伸手將眼睛哭紅了的女兒拽到教學樓角落裡,指著樓道遠處,甩出一句話:“你要是不讀了,直接從這兒跳下去。”
鄭漢超的父親有些擔心,自己的兒子是否也會成為“逃兵”。這個在氛圍自由的國際學校裡呆慣了的男生,已經開始抱怨“毛中太苦了”。
但是,“就像放進煉鋼爐的鐵塊,不可能再伸手往回撈”。平日裡嬌生慣養的兒子,“在這裡吃苦,受委屈,甚至個性被壓抑,統統可以接受”。
“其實,這真是中國教育的悲哀,但也是合理的存在。是體制錯了,還是勤奮錯了?”這個殷切盼望兒子考上大學的父親反問。
鄭漢超還算“爭氣”,他把iphone5扔進抽屜裡,換了一個在鎮上買的款式老舊的手機,不能上網,隻能用來打電話和發短信。
這個在微博上擁有11萬粉絲的男生想起,應該跟關注自己的人們短暫告別一下。他又掏出手機,發了一條微博:“你們一直抱怨這個地方,但是卻沒有勇氣走出這裡。9個月,咬咬牙,我們不在同一個地方,卻有著同一個目標,請等我回來。”
不過,鄭漢超並不想告訴朋友們,“這個地方”是毛坦廠,一個被人們視為誕生高考“神話”的地方。
從以“三線”廠為榮,到以“毛中”為榮
9月初,毛坦廠鎮政府辦公樓的玻璃門上,貼著大紅色的高考喜報。
官方對外展示的地方簡介裡,毛坦廠中學佔據著最靠前的段落,高考成績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處筆墨。
對於這個安徽的山區鄉鎮來說,教育是當地發展布局裡的一張王牌。用楊化俊的話來說,學校是毛坦廠發展經濟的“引擎”。
這台“引擎”發動起來,給這個鎮子注入看得見的商機。數以萬計的外地學生和陪讀家長涌進毛坦廠,催生了當地特色的“房地產經濟”。
這些外地的房客,大多住在書店、超市或者農貿市場等的商鋪樓上,為毛坦廠當地居民帶來一筆穩定而又可觀的房租收入。
陪讀家長大多抱怨:“這裡的租金太貴了。”目前,鎮上對外出租的房子,最便宜的租金一年大約四五千,最貴的達到兩萬多元。在當地,“一家本地居民靠出租房,一年收入二三十萬,很正常”。
30歲出頭的王瑞,去年從江蘇常熟回到家鄉毛坦廠,扒掉家裡的老平房,蓋起一棟3層樓的“學生公寓”,“一年的房租收入遠超過在常熟開服裝店掙的錢”。但是,這山望著那山高,他還是感嘆:“我還是沒眼光,蓋房子太晚了。”
那些“有眼光”的當地人,敏銳地圍繞著毛坦廠的強力“引擎”尋找賺錢的機會。
去年,金安中學新打開一扇北門,又為毛坦廠鎮掘開一條積累財富的通道。短短一年間,新北門外那條命名為翰林路的水泥路邊上,一座座四五層的小樓拔地而起,如今成為部分當地人的“搖錢樹”。盡管由於工期緊張,有的樓房外牆還沒來得及被白瓷磚填滿,裸露著整面牆磚。
毛坦廠鎮,正在以制造高考“神話”的毛中為圓心,劃出一個中部省份山區集鎮的經濟圖景。幾乎與毛中崛起的節奏同步,毛坦廠鎮的經濟也開始有起色。這個土地面積緊張、工業並不發達的鎮子,還曾在2009年、2010年連續兩年擠進六安市經濟發展綜合實力20強鄉鎮。當地政府介紹,去年毛坦廠的財政收入將近1500萬元。這個數字,是鄰鎮東河口全年財政收入的近4倍。
鎮政府的楊化俊說,毛坦廠從過去以採茶和賣竹子為主“山口經濟”,發展成為現在的“校園經濟”。
在這個擁有明清徽派老街的老鎮上,當地鎮政府還想打好一張旅游牌。不久前,一條超過千米的明清老街路口,建起一家仿古徽派建筑的“毛坦廠老街游客接待中心”。但是這個嶄新建筑物的棕色鏤空玻璃門如今卻緊閉著,門前還立著由三根竹竿搭起來的晾衣架,上面挂著女人的裙子和內衣。
相比於起步較晚的旅游業,由毛中帶動的校園經濟,能為毛坦廠鎮帶來更穩定的消費市場。楊化俊算了一筆直觀的經濟賬:“毛坦廠將近3萬學生和家長,如果保守估計,每人每天在鎮上消費10塊錢,全鎮第三產業一天的營業額至少30萬。”
有時,面對由毛中這台引擎發動起來的市場,毛坦廠這個小鎮子也會應接不暇。那些無力承載的消費需求,就會轉移到附近的鄉鎮或者縣城,成為周邊地帶的福祉。
70歲的本地人熊春義很難想象,毛中是如今鎮子的中心地帶。他更懷念上世紀60年代,坐落在毛坦廠李家沖村的“三線廠”,曾經為這個鎮子增添的繁榮景象。
“三線廠”是特定年代的產物。在1964年至1980年,國家在屬於三線地區的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投入巨資,號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民工,在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建起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當年,毛坦廠這裡建起一個生產槍支和汽車配件的軍工廠。
9月初的一個下午,干瘦的熊春義老人,蹲坐在牆皮剝落的灰磚樓門口,一邊搓著玉米棒,一邊回憶起有關三線老廠的畫面。他曾在廠區學校的食堂做工,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工廠搬遷到馬鞍山之前退休。
那些記憶,就像熊春義住著的這棟三線廠老宿舍樓一樣,已經很陳舊。
“那時,廠區是毛坦廠最熱鬧的中心,姑娘以嫁到三線廠為榮。”當然,他也知道,現在的毛坦廠人“以把孩子送到毛中上學為榮”。他的女兒在毛坦廠鎮區生活,以租房為生計。
即使沒有這個老人的回憶,如今看著遺留在這裡的廠房、醫院和學校舊址,以及牆壁上依稀可見的屬於那個年代的宣傳標語,也會引來毛坦廠年輕一代唏噓感嘆“不同時代的寓言”。
一位毛中的年輕老師說:“看上去這個廠區過去是多麼繁榮。讓我聯想到毛中,如今這裡也這麼繁榮,但不知道以后會如何。看來真是要居安思危啊!”
有關毛坦廠的一切
在毛坦廠呆了幾天后,來給兒子陪讀的湯才芳覺得,“這裡沒有新鮮事了”。
除了給兒子洗衣做飯,在毛坦廠剩下的大把時光,對她而言,隻能用“無聊”來形容。
一到傍晚,小鎮會熱鬧起來。三三兩兩的中年婦女,繞著毛中院牆外面的小路散步。隨著天色越來越暗,零零星星的人,逐漸匯成川流不息的人河。
在路燈下隨著音樂扭腰擺臀的人們,會給馬路岔口制造一些擁堵,惹得汽車司機拼命地按喇叭。
毛坦廠鎮的領導曾經表示,鎮上將來要建一個專門供陪讀家長們娛樂休閑的文化廣場。
鱗次櫛比的出租屋門前,頭發濕漉漉的女人們圍坐成一圈,談著家長裡短或者孩子的考試成績。腆著肚皮的中年男人,將耳朵湊到收音機旁邊,聽著黃梅戲。
湯才芳想給自己找更多的事情做。她跟房東“搞好關系”,要來一塊免費的菜地。她連夜翻了地,種上了大蒜和香菜。這個過日子精打細算過的女人,抱怨鎮上農貿市場的菜價“太貴了”。
種菜開始成為一些陪讀家長們所熱衷的打發時間的方式。毛坦廠一些棄耕的荒地,被重新撒上了蔬菜籽兒。那些找不到整塊荒地的人,隻好搗騰起學校院牆外面的土。初秋時節,小鎮時常彌漫著一股秸稈燒焦的嗆人味道。
近幾天,湯才芳在鎮上找到活計。她在離出租屋不遠的一個服裝店裡做縫紉工。晚上,當自己兒子正在教室裡埋頭苦讀的時候,她踩著縫紉機的踏板,為這個小鎮輸入勞力。
在毛坦廠鎮,有10多家服裝加工廠以及官方都不掌握數據的遍布於大街小巷的小作坊。那些踩著踏板的縫紉女工,絕大部分是鎮上的陪讀家長。
“現在正值服裝企業青黃不接的‘用工荒’,但是我們這裡基本不愁招人。”毛坦廠鎮上最大一家服裝企業的王領班說。
為吸引陪讀家長來做工,大部分服裝企業和小作坊會在招工廣告上寫著:“工資計件,工作時間不受限制”。飯點之前,這些女縫紉工必須扔下手中的夾克袖子或者棉服內膽,趕回租屋給孩子做飯。
楊化俊欣慰地向外人介紹,一家上海的大服裝廠,“看中我們這裡有大量的陪讀家長”,考慮落地毛坦廠鎮。
湯才芳並沒意識到,像她們這些來毛坦廠的陪讀家長,正在改變當地的勞動力市場。在她看來,除了兒子高考,其余消磨時光的活計,都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她聽說,毛中有一棵百年老楓樹。很多家長和學生拜過這棵“神樹”以后,“很顯靈,第二年高考漲了一兩百分呢”。
一天下午,湯才芳特意去尋訪這棵“神樹”。這棵老樹長得枝繁葉茂,一根長長的樹枝伸出學校的院牆。
走近毛中北門東側的那面院牆,湯才芳很震驚。觀世音菩薩的十字繡和“毛中栽培,神樹顯靈”的紅色錦旗,被鐵絲挂起來,幾乎遮住大半面斑駁發黑的牆。褪色的錦旗旁邊,一塊簡易房鐵皮搭起的棚架下面,香灰堆到1米多高,一大片牆皮已經被熏得脫落,露出紅色的裸磚。
湯才芳想燒上一柱香。巷子口,一個中年女人擺著香火攤,裝燭火的紙盒上兩個手寫的大字清晰可見:“狀元”。
這個陪兒子第二次沖刺高考的母親,在巷子口停留了一會兒,還是轉身離開了。她說:“信則有,不信則無。”
一些迷信的甚至說不清的神秘感縈繞在毛坦廠。很多學生會在高考前放孔明燈,希望獲得好運。但黃色是忌諱,因為那表示“黃了”。“送考節”那天,前三輛大巴車的車牌尾號都是“8”,出發時間是上午8點8分。頭車司機屬馬,寓意“馬到成功”。
如果真能熬到“馬到成功”的那天,鄭漢超考上了電影學院,這個未來的導演想拍的第一部電影,“就是有關毛坦廠的一切”。
(應採訪對象要求,鄭漢超為化名)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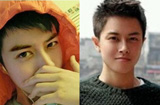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