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留下的這道疤

蔣寧從小居住的小山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言/攝

談起這場校園欺凌,蔣佑華總是眉頭緊鎖。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言/攝

吉首二中門前,“黑惡不除 社會不寧”的標語頗為醒目。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言/攝
2月的最后一天,18歲的湖南邵東小伙兒蔣寧拖著行李箱,要去廣東東莞“闖一闖”。幾天后,他站在了流水線,一天要站12個小時,先是一個月夜班,再倒一個月白班,每月工資四五千元。
離開前,爺爺蔣佑華反復叮囑他:“不要和那些偷、搶、騙的爛仔混在一起。”他回答:“你放心,這麼大人了。我進去過,我知道。”
“進去”始於4年前的一次校園欺凌事件。2019年5月,在湖南省吉首市第二中學(以下簡稱“吉首二中”)就讀時,蔣寧在學校男廁所遭到15個同學的欺凌,面對拳腳相加,他揮舞著折疊小刀刺傷了其中3人。經鑒定,兩人重傷二級,一人為輕微傷。蔣寧隨之迎來的,是長達11個月的羈押,以及3年半的訴訟。
2019年8月,剛滿15歲的蔣寧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捕。次年7月,一審法院認為,蔣寧屬正當防衛,將他無罪釋放。吉首市人民檢察院又提起抗訴,要求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兩年后,隨著上級檢察院、湘西土家族苗族州人民檢察院認為其“抗訴不當”,決定撤回抗訴,湘西州中院裁定准許,無罪判決終於發生法律效力。
蔣寧徹底摘掉了“犯罪嫌疑人”的帽子,但他的人生軌跡已經改變。抗訴狀態持續的兩年裡,蔣寧恐懼自己再被收監,也不願忍受同學們的指指點點,無心讀書。初中畢業后,他在一所職高讀了半年就輟學打工,在社會上“闖蕩”。
如果沒有這起事件,他現在也許正坐在高中的課堂,為高考努力。1米8的個頭,白皙的皮膚和標准的普通話,曾讓老師覺得他可以朝著播音主持方向發展。這一度是蔣寧的理想,如今他卻再也不想回到校園。而那次欺凌的3個主要組織者,至今仍在當地的高中、職校和體校讀書。
一場事先張揚的欺凌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欺凌,為了躲過它,蔣寧有過多次嘗試。
2019年5月17日,早上7點左右,蔣寧剛到學校,就被等在教室門口的同班同學孫翔帶著同學龍某喊去了廁所。在這所學校,“去廁所”有著特殊的含義。那是校園裡一個單獨的平房,緊臨穿城而過的峒河。“站在門口會看到廁所裡有煙冒出來。很多人在裡頭抽煙,上廁所都很難找到位置。”這是蔣寧對這間廁所的記憶。
案件材料顯示,蔣寧去了廁所,孫翔靠在廁所的矮牆上,邊抽煙邊問蔣寧:“我要打你,你怎麼辦?”他回答:“要打可以,但不要在學校裡打,放學后到外面單挑。”之后兩人便回到教室上早讀。
孫翔是班上同學眼中的“社會人”,其父母經商,家裡經濟狀況不錯,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獲得的案件材料顯示,多名學生曾向警方指証,孫翔喜歡和校外的混混玩在一起,參加了多起發生在學校廁所的打架斗毆。
孫翔為什麼要打蔣寧,法院判決書給出的理由是“性格不合”,但蔣寧一直納悶,何時惹了這個班上的“大哥”。此時已是他離開家鄉邵東到吉首就讀的第二年,3歲時,他的父親因病去世,母親也改嫁了,從小便由祖父母照顧在邵東山村裡長大,家人眼裡,他的性格多少有些要強。
小學六年級時,鎮裡領導來家裡了解情況,提出給他一些補貼,他梗著脖子和爺爺說,“不用別人資助我上學”。那時蔣佑華已年過六旬,村裡人建議他申請低保,“我孫子自己有志氣讀書,他都不要,我還申請低保?寧願自己苦一點。”蔣佑華也拒絕了。
蔣寧在鎮上中學讀初一時,母親莫蘭在娘家吉首市工作,一家人覺得“城裡教育資源好”,讓蔣寧轉學到350公裡外的吉首,重新讀初一。
2017年9月,蔣寧到吉首二中310班就讀,第一學期就被學校評為“優秀學生”,獎狀上還特別注明“年序68名”。但他始終覺得自己和這裡格格不入。這裡的學生大多說苗族話、吉首話,說普通話的蔣寧被視為異類。在班裡好友眼中,蔣寧是一個說話幽默、會活躍氣氛的人,成績也好,但有時開起玩笑來照顧不到別人的感受,“情商有點低”。
“沒什麼突出的,也不惹事。”在班主任的印象裡,蔣寧的數學成績很突出,學習成績保持在全班十幾名。“與本班同學相處融洽”,他在材料中証明。
2019年5月17日,早讀下課后去上廁所時,蔣寧遇到了孫翔和外班的五六個人。孫翔喊他過去,蔣寧沒動。一個身高力壯的同學就強拉蔣寧,有人從背后踢了他一腳。這時有人說上課了,蔣寧躲過一頓打。
此時蔣寧還不知道,他面臨的將不只是這幾人。上午第二節課間,孫翔在廁所遇到313班的胡峰、陳紅海等人,對他們說,“煩躁蔣寧,想打他,你幫不幫忙”。胡峰稱,蔣寧欠他一包煙,如果中午的時候不給,就要打他。
響應的還有陳紅海,他和胡峰同班,和孫翔也是小學同學,“他們打架我幫過忙。”他向警方回憶,那天胡峰曾在學校小賣部門口向班裡幾個同學表示,“蔣寧‘泡’了我的女朋友,想去打他一頓,打完之后叫蔣寧買幾包煙分給我們。”
蔣寧此前並不認識胡峰。幾天前,班裡乘車出去春游,他和坐在前排的同班女生說了幾句話,就被胡峰認為是招惹了他的“女朋友”,要他買煙賠禮道歉。他花7元買了一包“紅旗渠”,這也是他唯一能買得起的煙。母親莫蘭每天隻給他7元零花錢,兩元用來乘公交車上學,5元用來零花。那天,他選擇走路50分鐘上學,省下這兩元。胡峰沒收,在他看來,這是蔣寧“看不起他”,告訴孫翔“打蔣寧算我一個”。
很快,同學們知道了孫翔要打蔣寧的事。事后一名學生向警方透露,幾個人找到孫翔,希望他“莫打蔣寧”,得到的回答是“這個事情,你們莫管”。他們又找到蔣寧,讓他給孫翔道個歉,蔣寧也說不要管。他們覺得,“蔣寧平時比較好面子,我們也就沒管這件事。”
事實上,這個當時隻有15歲的少年有著自己的顧慮。一名同學后來告訴警方,他曾想報告老師,蔣寧反而勸住他:“給老師講了也沒用,今天不打,明天也會打我,還不如就到學校打,至少不會有校外的人參與,同學之間打架下手不會太重。”
蔣寧告訴記者,每到放學的時候,會有很多混混、社會青年在學校門口等,他曾親眼見到過很多次,同學在放學后在校外挨這些人的打。
今年3月3日下午,正值吉首二中放學,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該校門前恰巧目睹了蔣寧口中的一幕。幾名青年到校門前“堵人”,隨即被一名身著迷彩服的該校“教官”追出來驅趕,一路笑著從學校西邊的一條小巷跑掉,隨后一輛警車也趕到現場。
據記者粗略統計,在這所學校門前,至少有16個攝像頭。校門一側,一面藍色的警示牌寫著標語“黑惡不除,社會不寧”。
“我想拿刀嚇唬他們,讓他們不敢打我”
這場校園欺凌,蔣寧沒能躲過。胡峰和孫翔等人決定在中午提前動手,因為“放學難得等人”。
法院審理查明,2019年5月17日午飯后,孫翔帶著6個人到310班喊蔣寧去廁所,胡峰和另外7個人則在那裡等候。到教室門口,先是3個人進去喊蔣寧,蔣寧沒有理會,沒動。孫翔就自己進去,對他說,“如果你不去,我們就要強行把你帶過去。”
這樣,蔣寧被迫跟著去了廁所。臨走前,他把放在課桌內的一把折疊刀藏在了右手衣袖內。那是一把多功能工具刀,隻有手掌大小,班裡一名身體不好的同學平時用它來開藥瓶。刀是有人特意放在蔣寧桌子上的,至於具體是誰,他始終不願透露。后來他告訴警方,帶上它是為了在被打時,“拿出刀來嚇唬他們,讓他們不敢打我。”
廁所裡,孫翔、胡峰等15人把蔣寧圍了起來,蔣寧問,“你們哪個先上?”人群中個子高的陳東在眾人的示意中先動了手,他從后面用左手勒住蔣寧的脖子,把他摔倒在地,騎坐在蔣寧身上開始毆打,孫翔、胡豪等人便一擁而上踢打他。
毆打持續了1分多鐘,蔣寧掏出折疊刀揮舞,“他們打我打得很疼,當時我就想拿出刀來揮舞,讓他們不要打我”。突然有人說,“陳東,你背后好多血”,陳東發現自己身上受了傷,另一欺凌者吳某的左腿也被劃傷,雙方停手散開。
蔣寧從地上爬了起來,背靠廁所蹲坑的矮牆,無力地坐在地上。這時陳紅海從背后掌摑蔣寧,他轉身又向陳紅海腹部捅了一刀。其他人又上來一陣拳打腳踢,隨后散去,送受傷的人去醫務室。蔣寧嘴上不肯認輸,喊著:“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
蔣寧也受了傷,他的手指在流血,臉上和衣服上沾滿了廁所地板上的臟水。獨自回到教室后,他把刀扔進了垃圾桶,用自來水沖洗了手指,用紙巾簡單包了起來。
學校報了警。一位好友告訴蔣寧,有人在打聽他的家庭住址,揚言要報復。聽說這事后,蔣佑華連夜往吉首趕,班主任建議他把孩子帶回邵東老家,避免矛盾激化。在蔣佑華看來,這是正當防衛,以為最多就賠點醫藥費,就帶蔣寧回了老家。
2019年8月7日,學校轄區派出所喊蔣寧去吉首問話,他自此失去了336天自由的日子。蔣佑華回憶,當時一名民警告訴他,蔣寧涉嫌故意傷害,建議跟受害人協商,賠償醫藥費,取得諒解,孫子就可以取保候審。他找到了家屬,對方的要價是每人10多萬元。
母親莫蘭怕兒子在裡面受苦,想出這個錢。但她已重新組建家庭,又有了一個上小學的孩子,經濟上很是吃力。蔣佑華不同意,在他看來,就算出了這筆錢,如果被判防衛過當,留下了案底,將來也影響孫子一輩子。
這個老人20世紀80年代當過鎮上中學的語文教師,遇到同學間互相欺負,“隻要處事公平、有威信,你吼一嗓子就能鎮住學生。”家長大多來自附近農村的,校園欺凌鮮少發生。
在他看來,蔣寧是正當防衛。案發時,“昆山反殺案”正被社會熱議,還在2018年年底被最高人民檢察院列為指導性案例,明確正當防衛界限,進一步體現“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秩序理念,這堅定了他認為孫子無罪的信心。
2020年1月,吉首市檢察院將蔣寧移送起訴。該院認為,蔣寧屬於“約架”,還提前准備了刀具,是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重傷,應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
案件在吉首市人民法院一審開庭。法庭多方還原事實,特別納入了當時在廁所目睹整個過程的初一男生黃某的証詞。他不認識蔣寧,卻認識欺凌者中的幾人,幾次調查中的陳述也較為穩定。
一審法院認為,孫翔邀約蔣寧去廁所的行為不是“約架”,而是一種欺凌行為,這個時候無論蔣寧怎麼回答,都不能改變其被欺凌的事實,而蔣寧去廁所打斗也不是自願主動的,是在多人脅迫下經過兩次催促才去的。
在一審法院看來,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中,蔣寧自始至終均處於一種被動的、被欺凌的孤立無助狀態。從打架的犯意和傷害行為的實施,都是被動、被迫的。從早讀前被孫翔等人喊到廁所告知要被打,到早讀下課后第一次在廁所被多人拖、拽、圍、踢,再到中午被多人脅迫去廁所,到廁所后被多人毆打,整個事件的發生、持續、發展過程中,蔣寧都是被強迫、脅迫的,盡管他也說過一些“垃圾話”,但這些不能改變其被欺凌、被霸凌、被動應對的狀態及整個事件的性質。
一審法院認為,蔣寧為了預防不法侵害而攜帶的防范性刀具,目的不是為了實施故意傷害,而是為了對可能發生的不法侵害而進行的防衛准備,不影響正當防衛的成立。在被他人摔倒在地、並遭受多人圍毆、其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進行反擊、反抗的過程中,蔣寧刺傷了對他實施暴力的陳東、陳紅海等人,他的反擊行為也沒有超過必要限度。
2020年7月,吉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蔣寧無罪。
“一個巴掌拍不響”
失去自由336天后,蔣寧走出了看守所。這天是個大晴天,蔣佑華看到孫子走出來時,孫子大口呼吸外面“自由的空氣”。蔣寧對他說,他送進看守所的書,“都被我翻爛了”。那是一本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蔣佑華希望告訴孫子,“你的人生多災多難,但是你要堅強”。
此時,同學們剛剛參加完中考,包括那些欺凌者。蔣佑華帶他看望了班主任,老師鼓勵他,“回到家裡要繼續讀書,隻有通過讀書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為國家作貢獻,碰到數學有什麼難的,你再問我,給我打電話。”蔣佑華回憶。
蔣寧回到邵東老家的中學重讀初三。“剛開始表現很好,很珍惜讀書的機會,”蔣佑華記得,第一次期中考試,蔣寧考得很好,“你猜我們班上數學第一名是誰?大家都面面相覷,老師說是蔣寧。”蔣寧繪聲繪色地給爺爺講起了公布成績時的場景。
但很快,蔣寧平靜的學習生活被打破。2020年11月底,幾名檢察官來到他就讀的學校,把他帶到校長室做筆錄。原來,一審判決后,吉首市檢察院向上級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訴,要求以故意傷害罪追究蔣寧刑責。
吉首市檢察院在抗訴書中稱,“脅迫,應該是指讓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被迫的行為,而案發當時處於學校這一特殊環境內,蔣寧並非孤立無助,可以尋求老師的幫助,可以給家長反映,甚至可以坐在教室內對對方的無理要求置之不理。”
檢方稱,蔣寧沒有採用上述正當合法的維權途徑來保護自己,而是准備刀具用於斗毆,“被動應約,不能成為正當防衛的合理前提。”此外,蔣寧提前准備了刀具,在孫翔等人的兩次催促下,便跟著他們來到現場,並問“誰先動手”。檢方認為,從事實和証據表明,蔣寧准備刀具已經排除了防衛的可能,斗毆的意圖明顯,不能認定正當防衛,構成故意傷害罪。
對一審判決,當地也有一種意見,認為該案如果認定為正當防衛,那學生之間產生矛盾大家都動刀,“會對社會產生負面的導向”。陳東的父親在接受紅星新聞採訪時表示:“事情開始發生時,雙方都沒有向老師反映,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錯誤的,說他是‘正當防衛’,是說不過去的。”
“這對一個15歲的孩子是一種苛求。”蔣寧二審的辯護人、北京天平(長沙)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永紅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法院查明的事實顯示,當天蔣寧是在早讀下課后已經被打,此后連續幾次被喊出來威脅要打他,“要把事情發展演變的脈絡搞清楚,聯系起來看他為什麼反抗,完全是被逼無奈的。”
王永紅還強調,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於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其中規定:“未使用凶器或者未使用致命性凶器,但是根據不法侵害的人數、打擊部位和力度等情況,確已嚴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雖然尚未造成實際損害,但已對人身安全造成嚴重、緊迫危險的,可以認定為行凶”。
他認為,孫翔等人雖然未使用凶器,但是他們15人圍毆打蔣寧一個人,且先動手將他仰面摔倒在地,一擁而上拳打腳踢,已對蔣寧的人身安全造成嚴重、緊迫的危險,符合此規定的行凶認定標准。蔣寧面對危害自己人身安全的行凶行為,持刀防衛,即使造成兩人重傷的后果,也構成刑法規定的特殊防衛,不屬於防衛過當。
事實上,面對校園欺凌事件,蔣寧不是沒有尋求過學校的支持。2018年,他就曾成為校園欺凌事件的受害者。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獲得的案件材料顯示,打他的人叫向通,是314班的“大哥”,因為長期逃課,后被學校開除。那天課間,蔣寧在3樓的圍欄上張望,結果被在一樓的向通認為在“瞪他”。課后,學校組織拔河,314班又輸給了蔣寧所在的310班,獲勝后蔣寧興奮地大笑在向通眼裡很是扎眼。
向通糾集了一伙人,把蔣寧喊到廁所,要求他解釋“為什麼瞪自己”。盡管蔣寧反復解釋自己沒有瞪,但在圍觀人群“打他”的起哄聲中,一群人沖上去圍毆了他。毆打持續了幾分鐘,蔣寧隻記得當時“天旋地轉”。他的同學喊著報告老師,向通等人這才住了手。蔣寧頭部右側耳后的位置被一把木質折扇打得鮮血直流,醫藥費花了3000多元。
事后,雙方家長被叫到一起,由學校出面調解。結果是,施暴者的家長湊錢賠償了醫藥費,向通等人被記過。“當時學校處理的時候應該有記錄,但事情處理好后,學校好像沒有留底。”蔣寧的班主任向警方回憶。
但蔣寧被打一事也在學校裡傳開了,同學眼中,人高馬大的蔣寧因為此事“沒了面子”。而在蔣寧看來,學校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處理也是“不了了之”,打人的人根本沒受什麼影響,他甚至因此埋怨出面調解的母親莫蘭。在現場,向通班主任的話讓他記憶猶新,“一個巴掌拍不響”“怎麼不打別人就打你?”
這讓他不太信任學校對校園欺凌事件的處理。
“規定沒有落實到位”
一些教師認為,在處理校園欺凌上,自己也有難處。
蔣寧的班主任對警方表示,每年開學第一課就是安全教育課,會向學生宣傳安全知識,讓學生學會自我保護,如遇同學間發生矛盾,第一時間向老師反映。這一說法也得到了班上其他同學的証實。
這位教師在接受紅星新聞採訪時表示,蔣寧可能因為被向通等人欺凌存在一些心理陰影,自此不信任老師,但沒聽說他對處理結果“心裡不服”。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所中學任教過的楊濤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講述了教師們處理校園欺凌事件的苦衷:“我們近幾年防治校園欺凌宣傳和掃黑除惡進校園之后,也會給學生宣傳,出現問題,向老師和家長匯報。但有些孩子被欺負可能在廁所裡、在宿舍、在回家的路上,如果他不敢說,甚至欺負的人恐嚇他不說,確實很難發現。”
“基層面臨‘保學控輟’的壓力,很難管。學生的‘參考率’有指標要求,這就導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錯誤,隻要不是違法犯罪,肯定都是以教育為主,學校和公安機關的懲罰都是比較輕的。”楊濤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的一個學生,經常逃學、打架,和社會青年混在一起,還到鄰縣偷摩托車,被當地派出所抓獲批評教育后送回了學校。
“他主動給我講,我真的不想上學,我來就是影響其他同學,你們又要費心思管,我一點心思不在學習上。”楊濤回憶,這個孩子想回家,但校領導不同意,最后雙方妥協的結果是,縣裡抽考或者畢業考試時,學校給他打電話,讓他一定回來考試,“給學校的風氣帶來不好的引導”。有學生向楊濤抱怨:“我們表現這麼好,考試都是坐公交車去的,他表現那麼差,校長專車去接送考試。”
“又達不到進少管所的程度,工讀學校也要家長同意才能送進去。這樣一來,他們欺負別的孩子,學校隻能盡量協商處理,賠些醫藥費,讓他們下次不許打人,寫個保証書之類的,可能也沒用,實際懲罰力度很弱。”楊濤分析,在被打的孩子看來,可能就會覺得學校沒有處理,反正打人的人還要回到學校,“久而久之很多孩子受欺負就不敢說了。特別是有些留守兒童的家長不在家,或者隻有年邁的爺爺奶奶,根本無法處理”。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介紹,教育部2021年發布了兩個重要規章,分別是《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但很多地方“規定沒有落實到位”。
“有的老師認為他們缺乏手段,但是我們一定要摒棄一種思想,就是等問題大了再去處理,去開除、追究法律責任。”佟麗華解釋,懲戒不是目的,學校的目的是教育,一定是在小問題的時候解決,“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的前提是對違規違紀的學生進行懲戒,怎麼實施教育懲戒?什麼情況下實施教育懲戒?需要在學校制定校規校紀的時候就加以明確,成為有可操作性的規范。”
他還介紹,教育部提出了有條件的學校要設兒童保護專員,“在學校培養專業的人員,但是這個工作落實得也不到位”,可以通過發展未成年人社會組織加以補充。
3月23日,湖南省教育廳發文開展湖南教育系統防范中小學生欺凌專項治理行動,要求學校根據實際成立由校長負責的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建立防范學生欺凌和暴力行為早發現、早干預、早處置的常態化工作機制。
“失去的人生怎麼回來”
校園欺凌成了蔣寧心中的疤。
檢察院來找蔣寧的消息在老家中學不脛而走。他成了不少老師同學口中“犯過事的人”,很多人回避他,不跟他玩。他隱隱感覺,別人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這讓他感覺抬不起頭。
2020年12月25日,案件二審在湘西州中院開庭,蔣寧不得不坐火車來到湘西,第二次以“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回來后,他的心思已經不在學習上,他在看守所裡聽人說過,如果抗訴成功,他就要回到那裡,“辛辛苦苦把成績搞好,萬一又進去了呢?”
抗訴的壓力讓蔣寧無法釋懷。他發現手機游戲裡有另外一個世界,那裡的人不知道他的過往,每天在“峽谷”裡一起“打打殺殺”。老師一開始還勸他放寬心態,后來也慢慢放棄了。
有時他通宵打游戲,蔣佑華看不下去,多說幾句,蔣寧就“炸了”,“我又做錯什麼了?你又來說教。”蔣佑華能理解孫子承受的壓力,有一天早晨他喊蔣寧起床,“語氣可能嚴肅了點,蔣寧,怎麼還不起床?”睡夢中的蔣寧干脆地答了聲“到”,他說這是在看守所裡形成的習慣。
中考前,蔣寧把自己的作業本、書和試卷撕得粉碎,撒了一地,掄起家裡的椅子就摔。蔣佑華懷疑蔣寧得了創傷后應激障礙,但經濟條件也無力再給他做專業的心理治療。
遲遲等不到二審的結果,2021年7月,蔣寧的中考不出意外地失利了。他的成績隻夠上職高,一個學期沒結束就讀不下去了。他和朋友到社會上打工,因為未成年,他換了四五份工作,每次都不長久,做過飯店服務員、酒店服務生、網吧管理員。為了和“裡面”的生活相區別,他留了長長的頭發,還染成了黃色,還戴過耳環,“像變了個人”。
直到2022年11月,湘西州人民檢察院認為“抗訴不當”,決定撤回抗訴,湘西州法院裁定准許。拿到裁定書后,蔣佑華感覺蔣寧的精神狀態不一樣了,“表情生動了,話也多,大人說話也會聽了。”
一個月后,蔣佑華代表蔣寧向吉首市檢察院提交了《國家賠償申請書》,要求賠償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喪失受教育權及青春損失、精神損害撫慰金等。
2023年2月10日,吉首市檢察院作出決定:賠償蔣寧人身自由賠償金137538.24元﹔賠償蔣寧精神損害撫慰金68769.12元﹔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蔣寧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償道歉。
“吉首市檢察院的賠償決定,機械套用了國家賠償法司法解釋中,對精神損害撫慰金在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50%以下酌定的規定。”蔣佑華不服該賠償決定,認為司法解釋也規定,對特別嚴重等特定情形可以在50%以上酌定,“對損害未成年學生權益賠償沒有體現出來,對抗訴造成的精神損害和學業影響賠償決定書也沒體現出來。”
日前,他已向湘西州人民檢察院提出復議申請。3月17日,湘西州檢察院答復已收到復議材料,“經審查,符合我院受理條件,我院依法受理。將在收到材料兩月內作出答復。”
有人勸蔣寧,不妨出面用自己的本名,把這段經歷寫出來發在網上,“點擊率肯定很高,你也可以獲得流量掙錢,甚至比你的打工創業收入要高。”“你越怕別人指指點點,人家越戳﹔你越不怕,把真相說出來,反而大家都理解。”
但蔣寧都拒絕了。他推掉了多家媒體的採訪,去東莞找工廠打工。幾年打工中,他從不告訴身邊朋友自己的那些事。“不願意讓別人知道,怕被另眼相看。”
申請國家賠償那天,他給蔣佑華發微信:“你代表我去申請國家賠償和要求領導追責辦案的,賠償多少錢也挽不回我的青春損失和撫平我的精神損害。”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蔣寧、莫蘭、孫翔、陳東、胡峰、向通、楊濤為化名)
記者 劉言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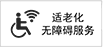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