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義:“勤靡余勞,心有常閑”
“勤靡余勞,心有常閑”出自陶淵明的《自祭文》,意譯“勤靡余勞”是一輩子勤勤懇懇,不遺余力。“心有常閑”卻與“勤靡余勞”相對,意思是心靈保持悠閑。梁啟超在《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一文中將“勤靡余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十六個字作為陶淵明“人格的總贊”,是對陶淵明精神特征的總體概括,這是很得要領的論斷。
這兩句話為什麼能作為陶淵明“人格的總贊”呢?從其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關系的角度思考,關鍵是其精義與《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血脈貫通。據高亨《周易大傳今注》,“天行健”的“行”有兩解,一是用作動詞,有運行之義,一是名詞,指道,且以“道”解為長。因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指上天運行遵循大道,剛健不已,君子也應效法上天自強不息﹔“地勢坤”的“坤”是順之意,順什麼呢?順天順道,因此“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指地順承天道,君子應效法地,厚德載物,兼容並包。如此,“勤靡余勞”就是陶淵明化的“自強不息”,“心有常閑”就是陶淵明化的“厚德載物”。“心有常閑”不是指簡單的閑逸,這種閑逸應是在“厚德載物”基礎上的,也就是說一個人隻有像地一樣敞開自己的胸懷,容納萬物,與萬物融為一體,這時遇到事情才不會為其堵塞抑郁,能從各種負面的情緒擺脫出來,從而保持“心有余閑”。所以,陶淵明的“勤靡余勞”“心有常閑”和《周易》中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息息相通,血脈相承的。
我們對陶淵明一般的理解是他很飄逸,但是我們仔細閱讀陶詩,會發現他的生活是沉重的,“勤靡余勞”“自強不息”是他人生的一個底色。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其三雲:“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這首詩被認為是一首寫得很飄逸和平淡的田園詩,人們把審美眼光更多地集中在“帶月荷鋤歸”一句中,鋤完地回家,把月亮帶回家,月亮走我也走,這是多麼飄逸和美麗的生活,但是我們也不可忽視了“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和“晨興理荒穢”,陶淵明晚年歸田后還有五個男孩子需要撫養,如果不去種地——他又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他從哪兒去獲得錢財養家糊口呢?所以說他必須去種地,因此41歲歸隱后,他有22年的躬耕生活。作為一個養家糊口的父親,發現地荒了當然會焦慮,一大早就去鋤地,勤勤懇懇地勞作一天,肯定很疲累,但也化解了焦慮,心靈暫時得以安頓,這時候才能有一種“帶月荷鋤歸”的感覺。因此沈德潛《古詩源》卷九評陶《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說:“《移居》詩曰:‘衣食終須紀,力耕不吾欺。’此雲:‘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又雲‘貧居依稼穡’,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異於晉人如此。”從內心接納辛勤勞作是陶淵明超越同時代貴族之處。
陶淵明的“勤靡余勞”為其詩歌的平淡飄逸打上底色,但這不是全部的陶淵明,陶淵明身上還有另一種精神:“心有常閑”“靈府長獨閑”。這種精神是魏晉風流留給他的印記,也受到他親近敬愛之人的影響,比如他的外祖父孟嘉。陶侃、孟嘉、陶淵明三人都能喝酒,但喜歡有深淺,作風有不同。史稱“(陶)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余而限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淒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逾。’”陶侃把喝酒的量嚴格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孟嘉喝酒的態度則是“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逾”有過量之義,陶侃“不敢逾”,孟嘉則“逾多不亂”,不因此違法亂紀,而是神情悠遠,旁若無人,與天地融為一體。陶淵明筆下的五柳先生“性嗜酒,……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以五柳先生自比的陶淵明在喝完酒后的率性態度與孟嘉更近,反而與陶侃遠,這正是不為俗羈、“心有常閑”的體現。陶淵明通過飲酒、借助酒的作用融化世間不平之事,厚德載物,胸懷曠達,達到一種超越的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講,陶淵明的心有常閑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勤靡余勞基礎上的超越精神,是立足於現實生活的閑逸。陶詩的閑逸與孟浩然《過故人庄》到朋友家裡過一個重陽節休閑不同,其原因就在這裡。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但是它們仍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義中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什麼呢?最高的境界當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我們在解讀《周易》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時,都往往容易忽視的前面六個字“天行健”“地勢坤”。“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是有根本、有依據的,它的根本和依據是天、地、自然,“天人合一”的“天”也代指自然,它類似用西方的話語所解釋的人類面對的客體,但是中國古人理解的“天”不單單是一個客體,而是應該敬畏和效仿的最高存在,與人的精神是合一的。在陶淵明,這個合一的境界就是“樂天委分,以至百年”,修身俟命,委運乘化,順應自然以至於“托體同山阿”。
有了以上對陶淵明精神的理解,我們再來讀他的《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會發現它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義的個性化傳達。
正是有了“心有常閑”這樣一種心境,陶淵明才能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詩、發現美,感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情景交融的意境,體會“天人合一”的境界。在這個境界裡,人生的各種煩惱、矛盾便像“厚德載物”一樣容納在他的胸懷之中,整個身心處在自由、自然、和諧之中。這種境界的獲得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了艱難的自強不息和勤靡余勞的努力。此一底色在他這首最飄逸的詩裡也隱約存在。這就是“結廬在人境”的“結”,什麼是“結”?“結”就像蜘蛛織網一樣,非常辛勤地去勞動,“結”可以看作一種勞動,你住的房子要去“結”,要去建造,而不應一伸手就輕而易舉地得到,甚至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去佔有。陶淵明建造的房屋不單單是一個房屋,在“結”的同時,他帶著自己的情感體驗和理想憧憬。這裡的“結”實際上就是“勤靡余勞”、自強不息在詩中留下的一個動作性符號。它是這首詩能夠進入情景交融、天人合一境界的一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詩境會像飄浮在天上的氣球,失去了拿在手裡的線繩,會破裂的。另外,要注意陶詩當中有煙火氣息,那便是“人境”,“人境”這兩個字也非常重要,他“結廬”為什麼要結在“人境”,這也是“勤靡余勞”的底色。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理想的境界不在天上,不在未來,就在人間,就在當下,最幸福的生活就是人間的幸福。所以,《桃花源記》描繪的幸福生活有勞作,有人間煙火氣息。這桃源的“往來種作”就是“結廬在人境”中的“結”,“設酒殺雞作食”就是“結廬在人境”的“人境”。所以說,“結”和“人境”在此處奠定了這首詩的根基,它的文化基因就在於“勤靡余勞”、自強不息,因為你隻有將這些筑穩了,你的心才能穩穩當當地“閑”,沒有外在、外物束縛的真正的“閑”。反之,總擔心哪一天會東窗事發,如何像陶淵明一樣住得很安穩自在?
是“人境”就會有艱難、苦惱,除了腳踏實地的努力,陶淵明用“心遠地自偏”去付出心靈的努力,即與世俗社會當中不符合真善美的事務保持一定的距離。“心遠”不僅是物理距離的遠,更重要的是心靈距離的遠,這就相當於在審美上為自己的心靈有意識地創造了一個存活的空間。隻有這樣,覺醒了的人,解放了的人,才是一個審美的主體,以這樣一個審美的主體去觀賞外物,你聽到的、看到的便不會是“車馬喧”,而是“東籬”“南山”“山氣”“飛鳥”,於是,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可以達到了。所以這首詩的最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實際上是已經從這個境界中走出來,為了更好地烘托進入天人合一境界的感受而作的結尾。
中國傳統文化最高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真正以詩歌這樣一種形式、用心靈去感悟到這樣一種境界的人是陶淵明,也就是說中國詩歌之所以有天人合一這樣一種境界、意境,中國詩歌真正能建立起個性化的詩歌意境,是從陶淵明開始的。
(作者:李劍鋒,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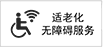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