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得:“我只是大海中的一顆小水滴”

圖① 胡思得參加國際軍控大會。

圖② 胡思得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辦公室工作。

圖③ 胡思得在西南科技大學作報告。
北京海澱區花園路6號院一棟灰色的4層小樓,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物院”,原二機部九局、九所)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館所在地。
11月15日,在所史館一樓展廳,記者見到了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物院原院長胡思得。
1958年,為了研制核武器,二機部在北京設立九局、九所。同年9月底,復旦大學畢業生胡思得到九所一室報到。
他告訴記者,1959年,為了給蘇聯承諾提供的原子彈實物教學模型提供“安家之所”,九所修建了廠房樣式的模型廳。然而,直至20世紀90年代被拆除,模型廳未等來任何原子彈模型。
望著空蕩蕩的模型廳,胡思得和同事們踏上了自力更生研制“兩彈一星”的征程。
“土方法”填補空白
1958年,胡思得報到時,室主任是鄧稼先。
“老鄧給了我們一本俄文版的《超聲速流與沖擊波》,讓我們去北京各大圖書館多借幾本。”胡思得說,但尋書無果,隻能自己動手油印。
“資料印出來后,我們一人一冊開始學,沒有人告訴我們將來要干什麼。”一個星期后,胡思得憋不住了,咨詢了鄧稼先。
“老鄧向上級請示后,告訴我們,九所是搞原子彈的,一室負責理論研究,並強調一定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胡思得聽后,心裡抑制不住地激動。
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條難走的道路。
“模型廳蓋好后,我們就開始等模型,但左等不來,右等不來。”胡思得說,后來,他知道,模型不會來了——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終止了原子彈援助計劃。
我國決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
“其實當時有人是持懷疑態度的,不相信我們能靠自己的力量造出原子彈。”但對胡思得來說,更多的是興奮和堅定,中國人終於要研制自己的原子彈了。
在鄧稼先的領導下,一室一直保持著互教互學的學術氛圍。
“比如研究狀態方程的時候,我因為比老鄧多看了幾篇文章,他就會讓我給大家講講。”胡思得回憶,大家就這樣你講一段、我講一段,把原子彈的基本理論吃透了。
胡思得領導的小組主要負責研究鈾的狀態方程。蘇聯原子彈用的裂變材料是钚,但我國那時沒有钚,隻有高濃鈾。钚、鈾的臨界質量不一樣,要進行原子彈理論設計,必須要掌握鈾的狀態方程,即高壓下鈾材料的密度、溫度、壓力和能量之間的關系。
在鄧稼先的指導下,小組成員從一篇英文文獻中找到了27種金屬的沖擊壓縮數據(也稱雨貢紐曲線),以及如何通過這些數據求解材料狀態方程的方法。
但27種金屬中並不包括鈾。鈾的狀態方程當時在國際上是保密的,國內也尚無實驗條件。
“小組群策群力,提出是否可以將27種金屬的雨貢紐曲線按各種物理參數進行排列比較,找到規律,進而推出鈾的雨貢紐曲線?”胡思得說,這個想法得到大家的認可,他帶領組員們分頭工作。不久,組員李茂生負責的一個參數呈現出明顯的相關性,團隊初步摸索出了鈾的雨貢紐曲線。
這僅是第一步。
雨貢紐曲線的適用范圍是幾十萬標准大氣壓以下。原子彈爆炸中,鈾所經受的壓力遠超這一范圍。如何將更大范圍內鈾的狀態方程計算出來,胡思得想出了一個“土方法”。
他把整個狀態方程分為了三段,對應三個范圍。在低於百萬標准大氣壓的范圍內,用自己推出的雨貢紐曲線。在幾億標准大氣壓的極端高壓范圍內,“借用”托馬斯—費米理論。之所以說“借用”,是因為此前這一理論被蘇聯專家認為隻適用於天體物理研究。兩個壓力范圍的中間部分,胡思得和同事根據上述兩條方程曲線兩端的走向進行外推連接,最終“湊”出了一個完整的狀態方程。
回憶起當初的“土方法”,胡思得笑著說:“這實在是被逼出來的辦法。”
對這個摸索出來的結果,誰也沒把握。
“這個時候,程開甲先生來到九所,給我們提供了很大幫助。”胡思得說,后來,他和團隊看到一篇蘇聯學者發表的論文,發現其處理大范圍狀態方程的方式與他們大同小異。這也再次驗証了胡思得等人方法的正確性。
后來,隨著理論研究力量不斷加強,相關理論研究水平也不斷提升,有力支撐起原子彈的設計、生產、試驗過程。
助力氫彈小型化研究
1962年下半年,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已基本成型,九所的工作重心轉入試驗、生產階段。從事理論設計的一室也開始著重關注理論與實際結合,為此專門成立了理論聯系實際小組,胡思得任組長。小組的任務是將理論設計方案帶到青海221基地,與實驗部門緊密合作,根據試驗結果指導實際生產。
周光召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出發前,他特意約胡思得談話。
“他對我說,搞科學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放過理論或試驗中存在的任何疑點。當理論和實際不一致的時候,最可能有新的突破。”胡思得一直將周光召的這番話記在心裡。
原子彈零部件對精密度的要求極高,導致成品率不高。這不僅拖慢了生產進度,也打擊了工人的積極性。院領導找到理論聯系實際小組,提出能否在保証試驗成功的前提下,放寬公差要求?小組在深入生產一線調研后,提出了一個想法:對加工難度較大的零部件,適當放寬標准,然后通過提高容易加工部件的標准來補償這種損失。
為了驗証這一想法是否可行,胡思得和同事們深入加工車間和試驗現場,親自動手測量、計算,反復調試,拿出了一套調整辦法,証明了這一想法的可行性。“我當時覺得很有意思,算是初步明白了理論應該如何聯系實際。”胡思得說。
胡思得和同事們的工作大大加快了原子彈生產研制進程,並且為后來指導第一代核武器工程設計、生產、試驗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晚,當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消息傳來,身在青海221基地的胡思得加入了游行歡慶的隊伍,喜悅填滿心間。
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后,胡思得和小組成員返回北京,被安排參與氫彈小型化研制工作。
氫彈小型化工作,關鍵點在於小。要變小,結構上必須要有重大改進,而結構的改變又會對裝置性能等各方面產生影響。
由於此前幾個核武器型號的研發工作都很成功,大家此時有些“輕敵”,忽視了可能存在的挑戰,使得這項工作從理論到試驗都出現了嚴重問題,導致了“三炮不出中子”事故。
“我們做了三次點火出中子的冷試驗,結果都不理想。”胡思得后來反思,“當初大家有些得意忘形,步子邁得太大。做核武器研究其實就像在懸崖邊行走,成功的道路隻有窄窄一條,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為了打響這一“炮”,隨后半年多時間裡,在鄧稼先、於敏的帶領下,胡思得和同事們堅持理論和實際緊密聯系,與試驗人員緊密配合,共同設計試驗方案,改進理論設計。
“我們齊心協力,一處處改進,冷試驗前后做了七十多次。對從結構設計到加工生產中的各個環節,我們都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胡思得說,為了克服特殊構型對裝置性能的影響,他和同事們憑借在理論聯系實際中得來的經驗,巧妙地對一些零部件作用時間進行了相應調整,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
“最后一次冷試驗時,我們圓滿解決了此前的問題,打響了這一‘炮’。”胡思得說,在這次工作中,於敏等人實事求是、嚴謹科學的治學態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更懂得理論聯系實際,以及從理論和試驗的不一致中尋求突破的重要意義。
重心轉向核軍控研究
自參加工作以來,胡思得親歷了我國核武器事業從無到有的“高光”時刻,也見証了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核大國發展核武器事業的歷程。
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蘇等國已基本完成核武器研制所需的核試驗工作,要求全面禁止核試驗的聲音愈加強烈。彼時,我國新一代核武器正處於爬坡跨越的關鍵時期,一旦被迫禁試,將給我國國防事業帶來重大損失。
懷揣著對國防事業高度的責任心,已經病重的時任中物院院長鄧稼先聯合於敏啟動了一項重要工作,向中央遞交一份加快我國核試驗步伐的建議書。
為了寫好這份建議書,鄧稼先和於敏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組織了一個調研小組,對核大國的核武器發展水平以及國際上的禁核試風潮進行詳細分析。時任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長的胡思得也是調研小組的一員,他幾次奔走於鄧稼先的病床前,全程參與了建議書起草工作。
“老鄧當時剛剛做完手術,切掉了部分直腸,身子坐不下,隻能窩在一個汽車輪胎的內胎上,逐字逐句修改建議書,一邊改一邊疼得直流冷汗。”回想起鄧稼先,胡思得滿是敬佩和心疼。
最終,經過細致研究、反復修改,這份言辭懇切、深思遠慮的建議書日趨完善。
建議書遞交后,中央高度重視,我國核武器發展也按下了“加速鍵”。1994年,胡思得被任命為中物院院長,主要工作繼續圍繞建議書展開,組織領導了我國此后的歷次核試驗。
1996年7月29日,是計劃外增加的最后一次核試驗的日子,這一天恰逢鄧稼先去世十周年。在當日舉行的動員大會上,胡思得回想起一路走來的歷程,感慨萬分,動情地對大家說:“老鄧在天上看著我們呢,我們一定會成功!”
試驗當天,一聲巨響如約而至,試驗圓滿成功,這是中國最后一次核試驗。同日,我國政府鄭重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暫停核試驗。
暫停核試驗后,我國核武器事業該如何發展?這一問題,早在最后幾次核試驗期間,胡思得等人便已有所考慮。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胡思得等人率先開啟了中國最早的核軍備控制研究。1989年,科學與國家安全研究項目(PSNSS)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成立,胡思得任研究組第一任組長。PSNSS成為我國對外開展核軍控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1999年,從院長崗位退下來后,胡思得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核軍控研究上。2003年,中物院戰略研究中心成立,胡思得任首任主任。
如今,已經88歲的胡思得仍然關心核軍控研究。沒有特殊情況,他每天會去辦公室工作半天,有時還要與年輕人開會討論。年輕時多才多藝、身姿矯健的他如今飽受膝蓋退行性病變的困擾,走起路來離不開拐杖,有時還需人攙扶。他還戴上了助聽器。“好在眼睛還不錯,看書還不用放大鏡。”胡思得總是這樣樂觀。
當記者問起,他如何定位自己在我國核武器事業中的角色時,他笑著擺了擺手說:“我只是大海中的一顆小水滴而已。借助集體的力量,我們可以波濤滾滾﹔如果離開了集體,很快就蒸發掉了。”(記者 都 芃 陳 瑜 吳葉凡)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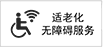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