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張晉藩在法大

“鑄就厚德品格,淬礪明法鋒芒”“行致公以追求社會和諧,勤格物以探索真理之光”……每當重大慶典,校歌《情懷法大》深沉的旋律便會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園中響起,學子們起身直立,深情高歌,唱響內心的情懷和追求。
校歌字裡行間訴說著詞作者、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先生對校訓“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沉澱與解讀,飽含著先生對法大學子“明朝國之棟梁”的殷殷期待,對矗立在軍都山下小月河邊的“政法教育殿堂”的深厚情感。
今年9月13日,張晉藩先生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表彰辭中提到:“新中國中國法制史學科的主要創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該學科的理論基礎和結構范式,為我國法學教育和人才培養作出重大貢獻。”
作為我國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新中國中國法制史學科的主要創建者和杰出代表,他在新中國法制史學上開創了多個“第一”:
招收了第一屆法制史學博士生、第一屆博士留學生、第一屆論文博士生,創建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法律史學國家級重點學科基地。
他的“早期”博士生大多已經退休,他卻還活躍在學術前沿,每天依然工作四五個小時。
70余年法史人生與教育人生,張晉藩先生在法大度過了40余年,也和法大一同繪出了別樣風景。他的人生譜寫出一部中國法制史發展的壯麗詩篇,也勾勒出幾十年來法大精神的代代傳承。
但使胸中豪情在,高天雲路續崢嶸
1982年,一封邀請開啟了張晉藩先生與法大40余年的深厚緣分。
當時,中國政法大學即將建立全國第一個法學研究生院,邀請他來主持研究生院工作、編寫研究生教材。張晉藩先生欣然應允,於1983年7月,正式調任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首屆決定招收17個專業、共計125名碩士生,並建立了相對獨立的、高效的管理機構——幾乎算“校中之校”的研究生院就這麼紅火地辦起來了。
然而,正當他准備大展拳腳時,殘酷的現實條件卻出了個大難題。當時的法大剛復辦不久,本就狹小的校園內有四個文藝團體混住,英語誦讀聲和吊嗓子練花腔的聲音交織,可謂是“熱鬧非凡”。硬件條件不行,師資也極為缺乏,教授、副教授加起來不到25人,隻夠入學人數的一個零頭。
“得英才”后如何“育英才”?
張晉藩先生想到了蔡元培先生主張的“兼容並包”思想:請校內外導師共同指導研究生。
從那天開始,他便往返於各個高校和全國人大、最高法等實務部門,聯系各路學者、專家擔任校外導師,組成各個學科的導師組指導教學。
著名學者王鐵崖、韓德培、孫國華、佟柔、高銘暄、張國華、蒲堅、蔡美彪、王家福、端木正等紛紛加入,還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張懋、人大常委會負責環保工作的曲格平……就這樣,法大成了當時國內一流專家的“聚集地”、學術與思想的“聚寶盆”,在還沒有“大樓”的校園中,學生們享受著“大師”們帶來的學術盛宴。
在經費緊缺的艱苦日子裡,相比吃住,同學們的學習條件卻是有些“奢侈”的。為了學好英語,學校外語課由外教擔任,每兩個學生還配發一台收錄機﹔為了開闊眼界,批經費給每位研究生每年提供一次機會,組織參加全國性的學術討論,同時邀請美國和日本學者來校講學……
錢要花在刀刃上,張晉藩先生堅持一切以學生為中心:“這對他們思想的教育,視野的開闊,刺激他們以后的努力好處太多了。”
法大的同學們沒有辜負他的期望。新中國第一批法學碩士、第一批法學博士都從法大走出,法學專業的第一個外國留學博士生也出自這裡。
卸去行政職務后的張晉藩先生在醉心學術研究與教育事業的同時,依舊關心法大的發展。
在研究生院院慶三十周年前夕,他寫下一篇文章,提出未來要在培養高端人才上下功夫,要為國家強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擔起歷史責任,字句間都是對未來的展望、對學生的愛護、對法大工作的期待。
今年4月,他捐資在海澱校區圖書館興建的“薊門法史書苑”正式揭幕啟用,這是全國唯一一所以“法律史”為主題的書苑。書苑入口,他親筆題下楹聯:“歷千年歲月締造中華法系,讀萬卷藏書譜寫法制文明”,時刻提醒著入書苑的學子要靜心讀書、悅己越己,以傳承法治文明為己任。
苦戀文字雖雲苦,書沒深山有余名
2024年,《張晉藩全集》第一輯出版,距張晉藩先生1954年在《光明日報》理論版頭條正式發表第一篇文章,恰好跨越了70載歲月。
70載學術人生,“著作等身”這一形容甚至有些保守。出版60余部專著、主編20余部中國法制史教材,可以說他是真正將“文字工作”做到了極致。《全集》僅第一輯就有22冊、約900萬字,排在桌上足有近一米長﹔全部三輯預計將達3000萬字。如此“高產”的背后,是他心中深沉的家國情懷和幾十年如一日的筆耕不輟。
張晉藩先生出生在九·一八事變前一年的沈陽,偽滿洲國日軍對東北人民的壓迫、學校中奴化教育和被扭曲的中國歷史讓他意識到侵略者“欲亡其國者先滅其史”的狼子野心,也燃燒起強烈的愛國熱情。這種對歷史、對國家的熱情也成為貫穿他整個學術生涯的線索。
因此,當他得知世界上召開過三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卻沒有一名中國大陸學者參加的時候,便立下一個宏願:要把中國法制史學研究的中心牢固地樹立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
1979年7月,長春,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舉行,張晉藩先生提議編寫《中國法制通史》多卷本。於是時間的齒輪開始轉動,等到這部總計超500萬字的鴻篇巨制終於完成之時,已經過了19年。
書籍編寫困難重重,時斷時續。會議次年召開的“集學界全部研究力量”的第一次編寫會,實際僅有二十余人參加。在尚無“一鍵檢索”的年代,沉於卷帙浩繁的史料,上至遠古氏族戰爭、下到新中國成立,徒手梳理中國法制發展歷史,並編寫出史料詳實、論証嚴謹的十冊書籍,其工作量和工作難度是難以想象和估量的。
“板凳要坐十年冷”,但這部“世紀之作”的編寫又何止耗費十年?19年來,面對經費短缺、出版困難,張晉藩先生四處奔走、籌措經費﹔當“超長戰線”下的人力不足開始顯現,部分編委退休、兩位編委謝世、兩位編委因感到出版無望退出后,他選擇拉上畢業的博士們一起加入編寫隊伍中,最終成就了這一部“世紀之作”。
翻開書冊,全書作者共計50余人,其中一些“年輕”的名字,如朱勇、劉廣安、高浣月等師從張晉藩先生的博士們赫然在列。透過泛黃的紙張,似乎仍能窺見如今已成“退休老教授”的他們,當年在老師身旁埋首於書海中的青澀背影。
書籍的出版可以說是震動世界。它用翔實的史料論証了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是“諸法並存、民刑有分”的,打破多年來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古代隻有刑法、沒有民法的理論,展示了中國法律制度發展的先進性和科學性。也是從這套書開始,中國法制史學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了中國。因此,它除了被譽為“中國版的《查士丁尼國法大全》”外,還有個別名——“爭氣書”。
在總序中,張晉藩先生寫道:“十卷本的《中國法制通史》出版了,了卻了同志們一樁心願,但研究工作正未有窮期……我們要持之以恆地為中國法制史學的興旺發達而夙興夜寐,極盡綿薄。”
他真正做到了。除了通史的編寫,他的研究覆蓋了憲法史、民法史、行政法史、刑法史、監察法史、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史、比較法制史、少數民族法制史、中華法系等分支,編寫法制史教材20余部……貫穿古今、包羅萬象,他的研究仿佛穿針引線,編織成一張細密的網,完整建立起中國法制史的學科體系。
“法制史研究的是過去,但面向的是未來。”在張晉藩先生看來,中國五千年的法制歷史源遠流長,彪炳史冊,既是標志其文明高度的豐碑,同時也是支持我國當前治國理政和增強文化自信所需要的智庫,因此研究法制史重在“以史鑒今”。
70余年學術人生,張晉藩先生對自己要求始終如一,筆耕不輟。對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張晉藩先生總結說是“但開風氣不為先”。這種自謙和堅守亦能從他之前出版的文集《涓滴集》《求索集》《未已集》《思學集》名稱中窺見一二:於中國法制史科學道路上載欣載奔的他仍在上下求索、壯心未已、思學不怠。
把酒歡歌新歲月,薪火傳承待后人
研究生院成立次年,張晉藩先生開始招收首屆中國法制史專業博士生,這是當時中國政法大學唯一的博士點。
中國政法大學原副校長、原法律史學研究院院長、新中國第一位法制史博士朱勇的本科、碩士研究生階段都在安徽大學學習,他選擇來到法大師從張晉藩先生,並以中國法制史為終生研究領域,還是源自碩士二年級在西安參會的經歷。
1983年8月,第一屆法律史年會在西安召開。會上,張晉藩先生講述了國際上召開過三次中國法制史的國際學術討論會而無一名中國大陸學者參加的事情,另外論述了“諸法並存、民刑有分”的觀點,倡導按法律體系分頭研究不同的法典,開創新的研究領域。
這給了朱勇非常大的觸動。“先生對我們這些年輕學生和學者寄予了厚望,於是散會后,我們幾個在讀碩士生一起商量,都覺得要扭轉這種現象,自己必須出一份力﹔對中國法制史這一學科研究也更有信心、更有責任感。”第二年,朱勇來到法大報考張晉藩先生的博士生,同懷效鋒、鄭秦一同被錄取。
對於學生,張晉藩先生始終用心用情,實時關注著大家的學習和生活。朱勇在跟隨先生讀書期間,擔任副校長並兼任研究生院院長的先生事務繁忙,隻能利用午休時間到學生們所在的3號樓宿舍講學交流、檢查學業。幾人一邊煮面條、一邊談學術,其樂融融,從不覺辛苦。
在80、90歲高齡時,張晉藩先生仍堅持每年為法制史博士生講解開學第一堂課,定下研究的總目標和總步調,也定下“尊重歷史”這最基本的史德。
法律史學研究院副院長、《張晉藩全集》第一輯執行主編羅冠男是張晉藩先生的第四代弟子,他對張晉藩先生在94歲高齡依舊堅持逐字逐句地對博士生論文進行反饋指導,竭盡所能地傳授啟發深感欽佩。“博士生論文一本至少十萬字,我們指導學生基本也是翻著看﹔但先生是要把學生叫到家裡去,一段一段地讀給他聽、一個字一個字地進行指導,”她感慨,“這是我們很多年輕老師反而做不到的。”
在張晉藩先生看來,指導博士論文寫作始終是博士生培養工作的重中之重。2002年初,《青藍集》出版,其中結集了他指導的34篇博士畢業論文的摘要,2010年又出版了《青藍集續編》。文集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認可,是法制史人才輩出的最好實証,法制史的研究工作也真正實現了他所期待的“后繼不乏人,后繼更勝人”。書名取義“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蘊含著他對於學生們寄予的厚望。
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張晉藩先生曾飽含深情地說道:“想建設疆域遼闊的社會主義中國,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才是科學的總結,是歷史的總結。”這是他終身投身教育事業最深層也是最朴實的原因。
到今天為止,張晉藩先生已經培養獲得學位的博士生百余名。博士生再培養博士生,代代傳承如今已有五代弟子,可以說是真正的“桃李滿天下”。
一次採訪中,記者曾問:“假如有可能第二次選擇職業,您准備選擇什麼?”他毫不猶豫:“教師。”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樂乎?”這是張晉藩先生接受採訪時說的話,也是對教育家精神中“樂教愛生”的最好注解。
2000年,古稀之年的他在《未已集》自敘中寫道:“在生命的旅程上,我覺得還處於日麗中天,不是夕陽紅。”
2024年,94歲的他依舊不那麼“服老”,他說:“隻要身體能頂住的話,我還是要多讀一點東西、多做一些研究。”
他端坐於薊門法史書苑內,講話時精神頭十足,臉上笑意沉靜,身前鋪陳開的是他開辟的中國法制史學之路,身后跟隨他的是心懷遠志、身懷本領的代代學子,也是中國法制史學的未來。
(本文小標題取自張晉藩先生詩集《思悠集增訂本》)
(記者 李依純)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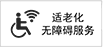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