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南文化交流的橋梁”(學海泛舟)
——我在南非做人類學田野調查
 |
朱鵬飛(右一)參加南部非洲人類學會年會與其他學者合影。 |
 |
朱鵬飛(右)與其教授合影。 |
幾年前,朱鵬飛作為聯合培養碩士在南非開普敦大學非洲研究中心開展了為期一年的訪學和研究,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進行海外實地調研,並因此與南非人類學結下緣分。后來,在中央民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朱鵬飛再次申請了赴南非的留學項目,並且順利獲得國家留學基金委的獎學金資助,前往開普敦大學進行人類學研究。
在南非課堂開拓視野
南非開普敦大學人類學系由英國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於1922年建立。2022年是開普敦大學人類學系建系100周年,百年來,其科研創新能力在非洲乃至世界都居於領先水平。我的研究議題是后種族隔離時期的身份認同與族群政治,重點考察南非的邊緣族群和社會底層群體,需要綜合運用政治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多門學科的理論知識。
我在國內多接觸中國和西方的理論,在使用這些理論分析南非當下問題時不夠切合。對此,開普敦大學人類學系的教授們給了我很多指導和建議,例如讓我多閱讀和了解南非以及非洲本土學者的理論著作、參加學術交流和田野實踐等。開普敦大學人類學系每周舉辦一次學術講座研討會,我得以有機會和來自南非以及世界各地的學者交流,這大大擴展了我的理論視野,加深了我對不同議題的理解。不過,真正讓我在學術上走向成熟的,則是田野調查。
在田野實踐中文化互動
不同於文獻研究,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是通過置身其中、觀察和深入訪談來獲取尚未被書寫的知識,它不是簡單的你問我答,而是一場有效互動的訪談,包含不少門道。比如訪談期間如何應對突發情況、怎樣更好地共情訪談者、如何對不同訪談者有效發問等。這些能力無法在課堂上言傳,隻能讓我們在田野中領會。
我的研究方法屬於多點民族志田野調查,在開普敦選擇三個不同類型的田野點。傳統的人類學田野點一般是以村落或社區為單位的靜態空間,現在田野點也可以是當地發生的動態事件。進入並融入每一個田野點,背后需要巨大的時間和情感投入。比如為了獲得訪談機會,我需要先進行大量的鋪墊工作得到對方信任,每條訪談內容寫到紙上或許隻有兩三行,但實際上需要我長時間的駐扎、頻繁到訪,盡量讓自己和當地人融為一體。
我的田野對象主要是當地貧窮群體,除了日常對他們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幫助外,我還嘗試通過自己在開普敦的人脈進行資源整合,為我所在的田野點社區搭建了一個合作項目:去年6月,在我的牽線搭橋下,一家當地華人文化教育公司和社區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建立了一項海外實習志願者服務項目。來自中國的大學生不僅將辦公軟件操作技能、工作報表統計知識帶給了當地社區,而且為社區人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許多歡樂。截至去年底,已經有兩批實習生通過該項目來到開普敦,他們住在社區進行半個月到兩個月不等的社區服務工作。這是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一項田野成就。
還有一次,我在田野調查中認識了當地的科伊桑人,他們喜歡詩歌,我為其中一位科伊桑人創作了一首中國格律詩,稱贊他為復興民族文化所做的努力與貢獻,我也借此機緣向他介紹了中國古詩的一些格式和韻律等知識,他們饒有興味。
除了在自己的田野點進行長期觀察與訪談之外,我還喜歡趁假期自駕旅行。這樣不僅可以領略南非美麗的自然風光,還可以在更大空間范圍感受當地不同的人文景觀,更加真實、鮮活地理解南非的多元文化與社會變遷。除此之外,我還力求擴大自己的田野訪談廣度,希望能從更大角度反觀我的田野案例。我不僅訪談過南非的憲法之父奧比·薩克斯等傳奇人物,也訪談過淪落街頭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通過與各類群體的訪談,我更加立體地認識了南非社會。
兩年的田野經歷使我深刻體會到一個道理:田野調查這種研究方式不僅僅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問答,更是人與人之間的文化互動﹔研究者不僅通過當地人認識了當地文化,當地人也通過我認識了更加鮮活的中國文化。
以學術增進中南人文交流
在課堂和田野調查之外,留學期間我還積極參加了許多國際學術會議、民間文化交流活動。比如我曾在2022年7月參加一場由南非北開普省政府舉辦的“藝術與精神健康”主題研討會,當時我以中國書法為例向南非朋友講解了書法中獨特的藝術美學,現場觀眾好奇滿滿,他們提了不少問題。此外,我還參加了幾次由國內高校舉辦的學術會議,向國內學者分享了我在南非的最新研究成果,希望為中南之間文化交流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我相信隨著更多學子走到海外,中外文化交流會走向人與人之間更深的互動。在南非的生活、學習經歷讓我對這裡的社會和文化有了更深認識,我願意以學術作為志業,做中南文化交流的橋梁,為持續增進兩國人文交流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開普敦大學人類學系聯合培養博士生)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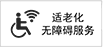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