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口不足50萬的山區縣,擁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3人,1600余人長期從事文學創作
走西吉,看文學“庄稼”茁壯成長(人民眼·新春走基層)
 |
圖①:小學生在西吉文學館研學參觀。 |
 |
西吉農民作家外出採風(資料圖片)。 |
引 子
書桌前,單小花提筆凝思,牆上“文學點亮心燈”的字幅格外醒目。她白天務農、打工,晚上擠時間寫隨感,已出版兩本散文集。
輪椅上,馬駿雙手捧書,看得入迷。他自幼患病無法行走,堅持躺在炕頭用手機寫作,前不久榮獲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小店內,趙玲一邊工作,一邊和顧客收聽文化典籍誦讀。作為一名盲人作家、按摩師,他創辦了“西吉縣殘疾人星光俱樂部”“慧覺文化學社”,幫助更多人從文學中汲取力量。
…………
這串名字還可以繼續列下去,他們都來自六盤山腳下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西吉縣。這個人口不到50萬的山區縣,有1600余人長期從事文學創作,其中農民作家超過300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3人、寧夏作家協會會員124人,先后榮膺魯迅文學獎、駿馬獎等國家級獎項6次,獲得人民文學獎、冰心散文獎等全國性文學獎項近40次。2011年,西吉縣被中國作家協會主管的中華文學基金會授予“文學之鄉”稱號。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202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著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重視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養全民族昂揚奮發的精神氣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結合、抓作品和抓環境相貫通,改進文藝創作生產服務、引導、組織工作機制。
一個曾經“苦甲天下”的山區縣,何以興起新大眾文藝的浪潮?記者近日走進西吉採訪。
一群農民作家
既扛鋤又拿筆,種農家地,耕文學田,寫出時代精氣神
白天,扛起鋤頭下地干農活﹔晚上,坐在電腦前敲擊鍵盤。西吉縣將台堡鎮明星村村民康鵬飛,已發表作品超過50萬字,文學是他的精神食糧。
康鵬飛自幼家貧,15歲初中未畢業就踏入社會打工。“日子過得如同晾衣繩,總是緊巴巴的,好像看不到舒展的希望。”對於那段歲月,康鵬飛有著難以磨滅的深切感受。
1997年,康鵬飛迷上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他說書中人物的奮斗故事“像一顆石子一樣扔進了我的心裡”,並就此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在務農與打工的間隙堅持文學創作,康鵬飛以文字養心性,創作的小說《夜班車》獲得全國首屆進城務工青年鯤鵬文學獎優秀獎。2016年,他以農民身份當選固原市文聯副主席。
與康鵬飛一樣,文學已成為當地不少農民侍弄的新“庄稼”。放下鋤頭握筆頭,耕罷農田耕硯田,他們在田間地頭構思、在燈下疾筆寫作。
“寫作和種地一樣,都需要辛勤耕耘,也都有發現的喜悅。”西吉縣吉強鎮高同村村民單小花,原本是普通農家婦女,2012年遭遇家庭變故,又患上重病。入院治療期間,為排解苦悶,她給女兒寫了一封信,恰巧被主治醫生看到。朴實無華的文字打動人心,醫生建議她聯系西吉縣文聯試試投稿。
懷著忐忑的心情,單小花敲開了西吉縣文聯辦公室的門,作品很快在雜志上發表,單小花收獲了平生第一筆稿費——300元錢。她像個孩子似的跳了起來,“當時,我在挖蒲公英補貼家用,挖一天才能賣20多元,300元稿費對我是巨大的肯定。”此后,單小花寫作的勁頭更足了。
地裡的蕎麥洋芋、家裡的牛羊雞狗、生活的點滴日常,都成為單小花創作的靈感來源。在生產勞作的間隙,她總會抬頭看看天空,瞧瞧周圍的環境,頓感心胸變得寬闊起來﹔尤其到了傍晚時分,看著山頭披上金黃色的“衣裳”,牛羊在泉邊暢快飲水,單小花更覺溫暖慰藉。
看著、寫著、讀著,單小花的精神世界日漸充盈,她直面家庭變故和身體患病的雙重打擊,靠寫作走出人生低谷。2019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苔花如米》,書名來自一句古詩“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單小花希望自己如苔花般勇敢綻放。
2023年10月,憑借100多萬字的作品,單小花正式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身為農民作家,我有責任講好農村故事,說出農民心聲。”單小花坦言,她不懂高深的寫作手法和技巧,但希望能如照相機一樣,實事求是地寫,寫出原汁原味的農村生活。她最想寫的,依然是身邊的農人農事、西海固大山裡男女老少的故事。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西吉作家們互相欣賞、互相激勵、“相親不相輕”。
“我的文學道路離不開朋友們的鼓勵與關照。一群像叔叔嬸嬸一樣的文學人‘團寵’著我,用愛意托舉著我,來到了這充滿大愛的文學世界。”獲得駿馬獎后,馬駿由衷感慨。
走進位於吉強鎮楊河村的木蘭書院,一群面龐黝黑的農民圍桌而坐,用夾雜著鄉音的普通話朗誦詩歌、交流創作心得,這是書院日常舉辦的一場改稿會。
“敞開心扉、暢所欲言,為的是寫出真正優秀的作品。”史靜波說。2019年,西吉縣作協主席史靜波創辦木蘭書院,並聘請了當地40多名農民文學愛好者,經常在改稿會上開展文學研討,帶動300多名鄉村文學寫作者創作。
除了木蘭書院,西吉縣還有詩詞楹聯協會、北斗星詩社等10余個民間創作平台。
“在這裡,文學之花處處盛開,芬芳燦爛﹔在這裡,文學是土地上生長的最好的‘庄稼’。”寧夏回族自治區文聯主席、作協主席郭文斌說,西吉的文學創作具有群眾性和規模性的特點,農民作家們吐露心聲,激揚精氣神。
一批文藝佳作
書寫山鄉巨變,記錄鄉村全面振興,作品與時代同頻共振
“發奮圖強,否‘難以生存’之定論。人造梯田,綠饒山巔﹔現代農業,遍地花開……”西吉作家樊文舉生於斯長於斯,創作了一首《西吉賦》,道出自己對腳下這片土地的贊美與熱愛,也揭開了它“難以生存”的舊傷疤。
西吉所在的西海固地區,曾被國際組織確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這裡生態脆弱、水資源匱乏、氣象災害頻發,有作家曾經這樣形容:“縱目所及,這麼遼闊而又動情的一片土地……有的只是這樣隻生絕望不生草木的光禿禿的群山,有的只是這樣的一片旱海。”
“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時候,人更需要精神力量。”樊文舉說,放眼皆是荒山,但文學想象超脫出一方天地,飛向無限廣闊的遠方。
翻開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西吉作家馬金蓮描寫道:“干燥的風裡含著很多肉眼看不見的細刀刃,把我們的手和臉劃開了無數細密的小口子……”隨著筆鋒一轉,又透出堅韌倔強:“但是這有什麼呢,從我們來到這個世上,從我們離開娘懷在地面上爬行的時候,開始在土院子裡一步一步學步的時候,風吹日晒的自然磨礪就開始了。”
“貧不薄文,曾經惡劣的環境和貧瘠的生活,讓我們對精神世界的追求迫切而自覺。”馬金蓮說。幾個月前,她的長篇小說《親愛的人們》出版,書的封面印著這樣的推薦語:生動還原中國鄉村社會現代化歷程,講述西北人民如何走向美好生活,書寫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堅韌與溫良。
1982年,國務院啟動實施“三西”(即甘肅河西、定西和寧夏西海固)農業建設專項扶貧計劃,開創了我國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減貧行動的先河。此后40多年裡,從閩寧對口協作到精准扶貧,在黨中央關懷下,西海固人民拔掉窮根。2020年11月,西吉退出貧困縣序列,標志著曾有“苦甲天下”之稱的西海固地區全部脫貧摘帽。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馬金蓮出生在西吉縣什字鄉一個叫扇子灣的自然村,這裡土地貧瘠,40余戶村民一度生活困難。精准扶貧政策春風吹來,扇子灣要易地搬遷。馬金蓮的第一反應,就是“要記錄這個村庄,要記錄這次易地搬遷,要記錄這群人,要記錄這個滾滾向前的時代。”
歷時多年,馬金蓮根據採訪所得和親身感受,完成著作《親愛的人們》。全書80余萬字,從20世紀80年代末寫到當下,圍繞西海固地區一個農民家庭脫貧奔小康的奮斗故事展開,呈現出一幅西部山鄉巨變新圖景。
村裡第一次通電、村民齊心協力修橋修路、村裡年輕人做起了直播帶貨……“時代底色是充滿希望的,我這本書的內在也是明亮的。”馬金蓮說。
書寫山鄉巨變,記錄鄉村全面振興。2023年底,單小花出版了她的第二本散文集《櫻桃樹下的思念》,專設“扶貧記憶”章節。
在往昔的艱苦歲月裡,文學為西海固人點亮一盞心燈,他們筆下的文字不乏光明與溫暖。摘掉貧困帽后,文學的根在這片土地越扎越深。西海固人對文學的熱愛純粹又熱烈,正續寫著家鄉的時代變遷。
當一篇篇反映西吉脫貧攻堅題材的小說、散文、詩歌等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西吉作家的筆下,貧困、苦澀、沉悶的氣息漸漸消退,山更綠、水更清、民更富的筆墨更濃。
“過去十年九旱,庄稼長勢不好,收割時隻能一把一把地拔。如今春麥換成了冬麥,產量翻了不止一倍,家裡余糧破天荒地壓滿了庫房。”康鵬飛回憶童年的艱苦日子,看到如今庄稼豐收,他根據生活經歷創作了《麥子》《糜子》等10余篇小說,描繪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
“辛苦了大半輩子,我把孩子供進了大學。現在政策好,生活沒那麼大壓力了,干農活之余就寫一寫。”吉強鎮高同村村民李成山年輕時愛琢磨詩,后來為生計操勞奔波,因生活壓力而放棄寫作,如今又因精准扶貧改變生活而“回歸”創作。他寫作的內容也發生變化:早年寫苦難,現在寫變遷,寫每年都在變化的新生活。
為此,李成山的小兒子很有感慨地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幾句:“我讀著三十年前的手稿/父親泡上一杯春茶/在甘苦回味間提筆/這一次/以農民的名義”。
“這一次,以農民的名義”。口袋鼓起來、腦袋富起來、生活美起來,新時代農民找回了自信與熱愛。
“種地時思考,閑暇時閱讀。”李成山見縫插針地用手機記錄生活隨感,描摹鄉村巨變,迄今已發表詩歌、散文300多篇。
黃河水深,黃土地厚。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是觀察新時代中國蓬勃發展的絕佳視角﹔推動農業農村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鄉村全面振興,是感受中國精神的時代現場。
作為親歷者,越來越多的農民受到洗禮,他們更加主動地建設家鄉,也更加自信地抒發所見所思所感。
“作家們以嶄新的敘事主題、審美形式,書寫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和精神蝶變。苦難正在淡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越來越多地被敘述。”寧夏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許峰如是感慨。
一個文學搖籃
出作品、育人才、樹品牌,文學之花處處盛開
路,無法用腳去蹚,卻能用“筆”去拓。
95后殘疾作家馬駿靠文學“站立”,去年11月榮獲駿馬獎的作品《青白石階》,是他躺在炕頭用手機一個字一個字“摳”出來的。
馬駿踏入文學家園的起點,可追溯至2018年底結識文學刊物《葫蘆河》主編樊文舉。在樊文舉的鼓勵下,馬駿在《葫蘆河》上刊發了不少作品。無獨有偶,單小花回顧自己的文學創作之路時也常提及:“我的第一篇作品發表在《葫蘆河》。”
在西吉,記者遇到的寫作者,幾乎都會提及《葫蘆河》雜志。
隆冬時節,朔風獵獵,長空寥廓,山腳下的葫蘆河已然冰封。對於十年九旱、山大溝深的西吉來說,葫蘆河孕育著生命與希望。
“葫蘆河是我們的母親河,所以西吉第一本文學季刊就叫《葫蘆河》。”這條河,將樊文舉的思緒拉回到上世紀80年代。
1987年,西吉縣部分文學愛好者成立了寧夏首個文學社——葫蘆河文學社,自費購買油印機和紙張,將他們創作的詩歌、散文刻字油印,裝訂成48頁的《葫蘆河》贈閱。
沒錢給作者發稿費,《葫蘆河》的編輯們就給每位作者認真回信,無論來稿採用與否。《葫蘆河》漸漸成為西吉文學主陣地,吸引了一批文學愛好者,文學社社員從7人發展到60多人,其中就包括作品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的作家郭文斌。
1991年,《葫蘆河》因經費、人員面臨困難,被迫停刊。2007年,在縣委和縣政府全力支持下,西吉縣文聯重新刊印《葫蘆河》,投稿人數不斷增加。
走進《葫蘆河》編輯部辦公室,樊文舉拿出一本即將付梓的樣刊。記者翻開一看,雖已審校過一遍,每篇文章仍滿是修改痕跡。
“西吉縣財政並不寬裕,但這些年來,每年12萬元的經費從來不少,讓我們能安心辦刊。”樊文舉轉過身,指了指牆上挂著的多幅照片,“你看,這些文化活動的合影,縣委書記一般都在場。”
2009年,西吉縣制定了創建“文學之鄉”規劃,成立以縣委書記、縣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並在全縣各鄉鎮和縣直部門設立基層文學藝術協會。此后,西吉陸續投入2000余萬元,建成了以西吉文學館為重點的10個文藝創作基地。2024年8月,寧夏首個中國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時代文學實踐點落戶西吉。
“從西吉走出的作家,不少都受到過《葫蘆河》的影響。”樊文舉說,這本雜志盡可能地接納、鼓勵創作者,並不斷提高辦刊質量,是西吉作家的搖籃。
2011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主管的中華文學基金會授予西吉“文學之鄉”稱號。13年多過去了,西吉縣文學創作者已從600多人增至1600余人,其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3人、寧夏作家協會會員124人,不少是新生代年輕作者。
西吉注重獎掖青年才俊,對文學苗子倍加呵護。在西吉“文學之鄉”命名10周年紀念活動中,10名學生被授予“文學新苗獎”。目前,全縣有校園文學社20多家、校刊20多種。
西吉中學月窗文學社已成立30多年,擁有社員200多人。“月窗”寓意“讓月光照進心靈的窗戶”。文學社創作的作品最初以手抄報形式刊發,也經歷過油印機印刷出版,現在仍在結集成冊。多年來,月窗文學社獲得過不少全國性榮譽,培養出一批批忠實的文學愛好者。
西吉人愛文學,文學又賦能鄉村全面振興。走進西海固農民寫作者的家,幾乎都能看到碼得整整齊齊的書架,攤著紙頁的書桌。文學給他們提供了生活支點,也成為他們自我教育、自我培養的有效途徑。通過讀書寫作,他們影響著自己的家人、孩子,帶動家風、鄉風改變,為發展鄉村文化注入內生動力。
文學澤被鄉野,木蘭書院所在地——吉強鎮楊河村即是縮影。村黨支部書記張世寶回憶,以前有的村民小組連續多年沒有高中畢業生,去年村裡一下子考出兩名本科生。木蘭書院假期向村裡兒童開放,村民們也經常能接觸到“大文化人”,潛移默化中,爭執糾紛都少了。張世寶說:“建書院比給村民發錢都好!”
依托獨特的文學資源,近年來,西吉縣探索“文學+農文旅”融合發展,先后建成西海固文學教育館、作家林等研學體驗場所,持續舉辦各類文旅節慶活動,擦亮“文學之鄉”金字招牌。2024年,西吉縣累計接待游客447.8萬人次。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曾說,“文學不僅是西吉這塊土地上生長最好的庄稼,西吉也應該是中國文學最寶貴的一個糧倉。”如今,西吉正鼓勵越來越多創作者拿起筆記錄新時代山鄉脈動,培育文學“庄稼”茁壯成長,讓這座文學“糧倉”更加豐足。
《 人民日報 》( 2025年01月17日 13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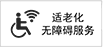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