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的當下責任
古之學者,多以“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任,於今之學者而言,承前啟后的學術使命,亦是應有之義。《詩經》傳統的悠久沉重,自不待言,當下研究的歷史責任中,既包含著兩千余年的經學傳統,更融匯了“五四”以來的現代范式,當代語境下的傳統延續、學術轉型則是仍在延續的深刻議題。
經學與文學
《詩經》研究的新、舊判分,大抵以“五四”為界。漫長的經學傳統於“五四”時期被重新估定價值,大有淵源的經學傳統直面來勢洶涌的科學思潮,《詩經》成為有價值的史料,進入現代分科體系下的文學視野。古老典籍與現代學科的遭遇涉及古今中西的學術對話。
熊十力曾言:“六經為中國文化與學術思想之根源,晚周諸子百家皆出於是,中國人做人與立國之特殊精神實在六經。”(《論六經》)一代大儒的經學情懷於中可見,然文章中的時代語匯亦屢屢出現。其言“孔子於《詩經》,明明昌言革命”。又稱“(興觀群怨)四義宏深,正是革命精神,卻從詩教涵養得來”。對於《詩經》之定位,雖保持經學之視角,卻也談道:“《三百篇》皆來自民間,今所謂大眾文學是也。”作為“大眾文學”的基本定位與一般關懷已然沖淡了《三百篇》的經學意味。稍晚的顧頡剛更以“結束經學”為任務,此后的《詩經》被納入文學史,有著歸屬明確的學科屬性,在科學觀念的系統整理下,成為樣式整飭的文學知識板塊。就《詩經》的知識接受而言,文學史居功至偉,無論是日后進入專業學習的學生,還是普通閱讀的一般受眾,對於《詩經》基本認知,多本於此。
此時期“中國文學史”的編撰者,即是當時古代文學研究的先導﹔而那些“中國文學史”的讀者,亦在日后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詩經》自不例外。對於《詩經》的專門研究遵循著語言、藝術、思想等“文學史命題”展開。隨著研究深入,“文學史”框架下的《詩經》命題多已成熟完備,論著頗豐,研治者不免有“話已說盡”的感覺,頗有“研究做完”的困惑,回視百年的學科反思應運而生,從觀念到模式的西化影響則是最為集中的審視話題。中國學術如何走出西方范式,成為當代學者的積極探索、勇於擔當的自我使命。落足於《詩經》,最鮮明的體現則是經學傳統的逐漸回歸。《詩》之為經,本是無法割舍的傳統﹔《詩》之為詩,則系與之俱生的天性,對此原態的雙重認可成為《詩經》研究之中國模式的邏輯起點,視野的轉換造就了史料的豐富,語境的還原貼近了歷史的真相,傳統的續接凸顯了思想的深邃,中國學術的文化自信亦於中逐漸凸顯。
文獻與方法
一般而言,《詩經》研究的重要元素有二:一是文獻史料,二是研究方法。前者重在“做什麼”,后者強調“怎麼做”,前者是基礎,后者是手段。《詩經》文獻史料主要包括歷代《詩經》著述,及一些近人著述,寬泛一點,還應包括經學著述之外的《詩經》資料,諸如在筆記、詩話、別集等文獻出現的相關資料。以古籍影印而言,四庫系列、叢書集成、清經解等大型圖書的出版無疑為史料的獲取提供了相當的便利,作為專書影印的尚有《詩經要籍集成》,涉及《詩經》著述百余種。此外,尚有《詩切》《詩毛氏傳疏》等數種,稱引最繁,最具影響者則為阮刻《十三經注疏》中的《毛詩正義》。古籍文獻的影印儲備,基本保持了《詩經》著述的原始面貌,更使得大量深藏散見的歷史文獻成為普通學者可以觸碰觀覽的研究資料,甚有益於學界。存世古籍是《詩經》研究的基本原點,相關文獻的搜集、整理、闡釋則是學術遞進的必須台階,其中,關於古籍的點校、整理是普通而重要的一環。史料為學術之本,古籍整理作為研讀史料的基礎工作,雖系看不見的功夫,卻是學術走向縱深所不應忽略的有力支持。然而,關於《詩經》古籍的整理,雖未中斷,卻興趣有限。
古人句讀,意在讀書之方便、理解之准確。“五四”以來,借助新式標點的古籍整理,一面以傳承古典為念,一面以今人接受為便。顧頡剛曾整理王柏《詩疑》、鄭樵《詩辨妄》等,得風氣之先。“叢書集成”中排印的部分《詩經》著述算是較早的整理成果,然數量有限。20世紀五六十年代,條件所限,僅《詩集傳》《詩經通論》《詩廣傳》等得以點校出版。八十年代,大為改觀,各種叢書、全集逐漸出版,其中涉及《詩經》者,如十三經清人注疏叢書、《清詩話續編》、山左名賢遺書、安徽古籍叢書等。再如朱熹、呂祖謙、顧炎武、王夫之、戴震、焦循、康有為、廖平等人的全集中亦收錄相關《詩經》著作。此外,獨立出版的《詩經》文獻不過《詩經原始》《韓詩外傳》寥寥數部,學界的興趣態度可見一斑。
與文獻之“冷”相為對照的是方法之“熱”。與古籍文獻的傳統屬性不同,對於方法的強調被視為現代學術的重要標識。從“五四”學者對科學方法的熱衷到時下研究方法的層出不窮,對各類方法的追隨在相當程度上指引著現代學術的發展路向。走出經學的《詩經》,不僅以民族文學之源的姿態進入與后世文學及世界文學的比較觀照,更以先秦文化史料的樣貌進入禮樂傳統和民風習俗的社會分析。毫無疑問,新方法的引入,於傳統經學外“開辟門戶”,涉獵之廣,遠愈前代﹔視角之新,超邁古人。現代《詩經》研究,於新方法得益最多,創獲尤多,各種“新解”“新論”“新說”層出不窮,論者多能發前人所未見,令人耳目一新。盡管歸根結底來說,現代方法與傳統典籍並不能十分適應,但方法的“趨新”仍在社會科學方法與范式的影響下,成為《詩經》研究在現代的標志性特征。
成績與困境
《詩經》研究的現代成績自是煌煌,從經學到文學,從舊文獻到新方法,從普及鑒賞到專門研究,從學術機構的成立到大小課題的設計,諸般種種,幾乎涵蓋所有關涉《詩經》的可能領域,全面展開的學術探索,既有舊學傳承,亦有新知融匯,不同層面的學理交匯,不同角度的觀念沖突,不同形式的成果體現,成為現代《詩經》學的最為鮮明的多元化特征。《詩經》詮釋的現代化,秉承現代科學精神,日趨嚴密的邏輯論証,視角多元的研究取向使之全面展開,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在橫向研究上取得了成功,而學科建設的理性和眼光則從梯隊培養、機構設置、資料准備、學術史整理等方面加深了《詩經》詮釋的縱向深度。二者相互促進,推動了《詩經》詮釋的全面發展,成績斐然。
現代《詩經》詮釋全面開花,與之相應的則是成果數字的驚人增長。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緩步增長,再到改革開放后的逐步繁榮,乃至21世紀以后的龐大成果量。以《詩經》研究而言,在1978年至2000年間,共發表論文約4300余篇,短短23年,還不及百年《詩》學的四分之一,而研究成果已達總數的79%。進入21世紀后的論文數字,更是一路飆升。數字的增加,自是學術繁榮的象征,然而,超量的數據卻沒有帶來學術創新的大發展。“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古訓於數字的激增中漸行漸遠,功利指向下的精神流失成為學術前行的最大困擾。
當代《詩經》論著的數量令人瞠目結舌,隱於其后的重要原因正是學術功利化、考核數據化、評估表面化。如此學術生態下的《詩經》研究不免功利,將“我注六經”的隨意游談發揮至極。“年均八百篇”的作者群已然超過讀者的數量,近百種的《詩經》注釋有多半是無人問津的,而文獻扎實,功底深厚的上乘之作卻淹沒於龐大數字,不得不面對“劣幣驅逐良幣”的尷尬。龐大數據的制造者們,不僅是當下學術的讀者與接收者,更是未來學術的作者與傳承者,最是令人深思。
皓首窮經,原無貶義,乃是褒詞。以經學古籍浩瀚典奧,須有相當時間精力的專心投入,方冀有成。最初的輕視來自科舉之下的功利心態,所謂“皓首窮經,方諧一第”,一個“方”字道出了投入產出的不成比例,“窮經”遂為人所輕。“著書都為稻粱謀”,功利導向下的捷徑選擇,自古已然,不可完全歸咎今人。所需留意的是,現代科技對於捷徑的推波助瀾。電腦、互聯網、信息技術等,已然從便利工具成為生活必須。隨著電子文獻與搜索技術的飛速發展,“窮經”無須“皓首”,不過鍵盤彈指之間。方便快捷,自不待言,更造就了數字的激增。搜來的材料終非讀書所得,比比皆是的研究成果與蕭條暗淡的《詩經》文獻,其間微尚可知。“束書不觀”,最是古人抨擊所在,而今卻成為科技捷徑下的普遍形態。當流於表面的數字進步日漸成為學術發展的新標識,外部工具取代內在閱讀的時代潮流已然成形,敢不發人深省。
經學傳統與文學學科,文獻研讀與科學方法,技術手段與讀書精神,涉及古今轉換、中西匯通、內外交融的諸多命題,自須調適面對,甄別處理﹔於《詩經》研究的當下責任而言,須時時提醒的初心所在,則是“學以為己”的古人訓告與“更愛真理”的知性反思。
(作者:賈娟娟,系山西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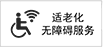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